|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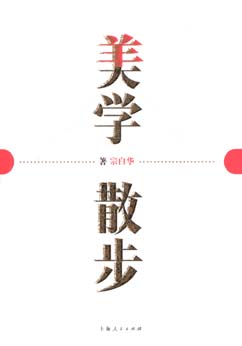 前些日子看了本美国人宇文所安的《追忆》,说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前朝后世的诗文,在作者看来,前后始终因缘相牵,“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于是,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诗文,既是它们的前尘旧事,也代代承传为我们的记忆和追思,好比“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 前些日子看了本美国人宇文所安的《追忆》,说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前朝后世的诗文,在作者看来,前后始终因缘相牵,“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这个世界为诗歌提供养料,作为报答,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于是,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诗文,既是它们的前尘旧事,也代代承传为我们的记忆和追思,好比“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
我喜欢这种打破时空,不拘泥于写作背景和文学史框架,而沿着个体生命对文学的体贴和感悟去兴会去研究的方式,在《追忆》里,也有历史佐证,也有身世参考,但这些都融会于宇文所安对作品的理解、感受和思悟中,他是将作品当作了山水草木,是独立客观的审美对象,不是社会或历史的附庸。同时,他的表述也是文学性的,《追忆》读来于怡然间获得审美/知性的快乐,甚至获得另一种感受古典文学的思路,而非当下盛行的某种“规范论文”,“后现代”“殖民地”“某某主义”等舶来名词概念一大堆,弯弯绕的不知所云的长句子是铁了心要让人云里雾里,否则无以表示“学术”的堂奥,宇文所安说《追忆》是他“尝试把英语的‘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因为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也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说得好,也做得好。
“中国式的感兴”,似乎在中国人中倒不怎么受推崇了——那仿佛属于古人的专利,钟嵘、司空图、刘勰等,而当下,是言必称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西人西语的,倘非如此,实在显得不够国际化和“与时俱进”的。那种中国式的感兴,写得再好,也难以上核心期刊吧;个人生命体悟,那似乎更让人笑话理论幼稚,归不了“体系”“谱系”一类了。看《追忆》时,格外想念一个人的文字,他的《美学散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时要取出翻阅,常看不厌。今年春从《新民晚报》丁聪“文化人肖像”专栏恰好也看到了他——宗白华,诗人、美学家,顿时语默心动,感念静祷。似乎正应了一种时光里丝缕不绝的“追忆”。
《美学散步》包括前言后记也才262页,较动辄大部头的一些“著作”显得薄了些,似乎也不讲究个系统体系,是美学论文的汇集。记得初次相遇,欣喜若狂,感觉差可比拟初恋,但更妙,因为没有苦涩,只有美妙和回味。是从这次散步中,初步体悟了“文艺的空灵和充实”,了解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和“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触摸到了“《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以及关于园林的飞动之美、中西绘画的不同空间表达、罗丹雕刻、康德美学思想、艺术表现的虚与实、中国古代音乐寓言和音乐思想,等等,可以说《美学散步》在一个不到20岁的学子身上投下了一束优美神圣而气象万千的美的光,开启了一个个体生命的艺术美感的心灵,静照和感悟,以及体验。在那时期所阅读的一些文学艺术和美学书籍中,《美学散步》给我一种光明莹洁、烟波浩淼之感,它是在一种优美的散文笔调中展开美学讨论的,甚至能让听到作者本身的心灵脉动。既是学术,又是美文,寻文学艺术之美味,寻美学与人之心灵相契的美妙,这样的《美学散步》就如同漫步在草木华滋山色空的风景间,理趣智趣情趣完全融为一体,通体舒畅开阔。
这种感受过去了很多年,却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进而二十一世纪,反而更加沉潜,甚而成为生命自觉的审美观照。只是如宗先生这样的“博学入精妙,哲理化诗情”(杨辛)的文章实在杳然了,仿如宗先生当年提出的“美从何处寻?”之问,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空谷回音,虽然我们并不缺乏“美学论文”的。何以如今文学/艺术的论述讨论铺天盖地,屈原之缠绵悱恻、庄子之超旷空灵的体悟却反而零星寥落了?如《诗品》《沧浪诗话》《艺概》般以性灵会通作品、慧悟精妙之中国风格的审美品鉴沉落于历史烟云?在所谓理性深刻之时,是否消失了一颗敏锐于“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之宇宙永恒的心灵?或者还有一种流连勾栏画栋的和谐、黑白笔墨的意趣和从容?我常常阅读《美学散步》,希望能在宗先生觉心空明又悠然意远的美学步径经常走走,仿佛一种“加持”。如苏东坡所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向往臻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之大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