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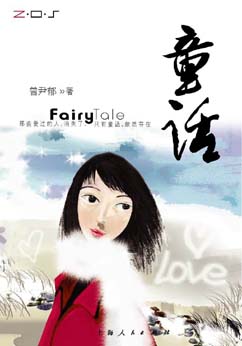 《新作文》:Z.O.S,能和你们对话很高兴。虽然不少读者已经很熟悉你们了——刘童和曾尹郁都已出过两本畅销小说,肖水也是“80后”成名已久的诗人——对《新作文》的读者,你们还是先简要地说下自己的近况,好吗? 《新作文》:Z.O.S,能和你们对话很高兴。虽然不少读者已经很熟悉你们了——刘童和曾尹郁都已出过两本畅销小说,肖水也是“80后”成名已久的诗人——对《新作文》的读者,你们还是先简要地说下自己的近况,好吗?
曾尹郁:我现在湘潭大学法学院读三年级,刚出过两本小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少年》和《青春不解疯情》。
刘童:我已经脱离了学生的身份两年了,现在北京主编一档日播的娱乐节目。我的小说是《开一半谢一半》和《五十米深蓝》,希望大家还能想起我。
肖水:我头顶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光环了。我现在复旦大学法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我们虽然演的是“三城记”,心却是在一起。
《新作文》:好!接着……我们都很年轻,有人说“成长中的少年”最大化地享受了“现代化”,并且陷入了“享乐主义”。但刘童似乎是一个警醒者,有一篇文章曾引发社会上对于“伤残童年”的讨论,是什么引起你对这种问题的关注呢?
刘童:所谓“伤残童年”,其实并非仅指肢体或器官的缺陷,而是指童年记忆的缺陷。那篇文章叫《那个女生叫开开》,作于大四。那时我发现,记忆在不断模糊,从而回忆变成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多数人的童年都因此残缺。于是,我试图逐个回忆自己所认识的人,发现每个人都对自己影响都很大,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可能因此而改变。开开是我的小学同学,智障,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所有人都不知道,只觉得她是傻子,于是大家都去欺负她。而作为她朋友的我,却只能旁观。多年过去,我很愧疚,童年对她的伤害,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对自己美好童年的伤害,这就使我们的童年变得不完整。
《新作文》:如今青春写作少有作品真正地关注这些严肃的话题了,但你们似乎在顽强地坚持着某种努力,这样的努力有怎样的意义呢?
刘童:“80后”多数人的写作是从“我”出发的,所有感触都以“我”的理解世界与社会的程度出发,在范围和经验上非常有限。如果“80后”从更多的“他”出发,将会对社会和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对比。“我”只是一人,而“他”则有千万。无数个千万才是社会,才是世界,才能够引起多数人的共鸣,才具有少许的社会意义。
《新作文》:这似乎反映了我们这一代视野的狭小与局限、精神世界的枯竭,这与“伤残童年”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关联的吧?从这个角度出发,你们觉得我们面临的世界该如何形容呢?
曾尹郁:我个人并不觉得我们的视野狭小、局限,精神世界非常枯竭,相比之前的许多年,我看到的是整体性的进步。新生代的人更独立,也更会思考。即使那种思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直觉般的排斥或接纳,但也说明了一种爆发和转变。我们更应该看到希望,就如海明威所说的:“这个世界足够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新作文》:如诗歌的美好,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我最早听说肖水是因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诗人”,而现在──好像是第一次出版作品吧──呈现给我们的却是长篇小说。在写作上,诗歌和小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请问你在其中是如何把握的?
肖水:80后的诗人在最近一年里,一直面临着诗歌和小说的取舍。如大家所知,80后文学的命名首先是从诗歌起步的,到了郭敬明等人锋芒毕露之后,这个概念才扩展到了小说写作。80后的诗人就像商品一样,他们期待着被人拿进购物筐里,但当代诗歌实无市场可言,于是出现了80后诗人的“集体跳水”──他们都跳到了小说写作的货架上。也许有人会说我也是那样一件急功近利的商品,迫不及待,改头换面,希望获得一个“好价钱”。但我想说的是,小说对我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并不会完全占领诗歌的领地。《恋恋半岛》断断续续写了9个月,其间我并没有放弃诗歌写作,反而我的语言受到了极大的锤炼,几首令人惊喜的诗歌出其不意地产生了。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我的诗歌和小说能有一个很好的进步,也期待着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不像大多数80后诗人那样趁夜色逃亡。
《新作文》:听说你们似乎都有过类似于“逃亡”的“漂泊”的经历,给我们说说好吗,这对你们的写作和成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刘童:对我来说,所谓漂泊,并非现实生活里的不稳定,而是目标的漂浮。我从郴州到长沙,从勤勤恳恳工作到义无反顾辞职考研,然后以一分之差与研究生失之交臂,再到北京工作。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漂浮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反复的过程。我不停思考,到底自己是谁,适合什么,属于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追求什么?建立,推翻,建立,再推翻,顿悟,行动。对于成长来说,虽然越漂泊越成长,但要在漂泊中及时给自己定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然漂到乱了方向,整个就玩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