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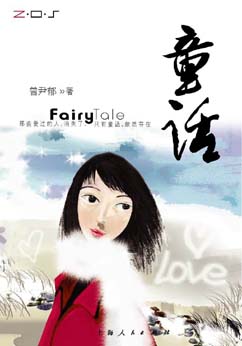 是从什么时候起,在小说创作中坚守独立的审美力量和形式价值,开始淡出作家们艺术探索的历程?就连很多曾经的“先锋作家”也接二连三地从这样的艺术命题中退场,降低了对生存和心灵追问的尺度和深度,“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披着“新写实主义”的外衣叙述生活的万千景象。小说的主题长期被寡淡而类同的现实奴役,看似在抒写生活的作品实际上是游离在现实的表层,这就致使文学出现虚浮的繁华,人们也因此一直对长篇小说怀有沉重的失望——关注现实确实拉近了与生活的距离,但却把阅读的想象都占为了它的殖民地。面对这种惨淡的景况,一个作家保持写作的责任和追问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尹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文本,他的长篇小说《童话》既完成了对生活内容的足够关照,又给物质之下人们空虚的精神和悬空的欲望以拯救和慰藉。这种不懈地而且具有一定深度地追问,使小说叙事在现实与想象中脱离单纯的场景和事件,表达出对生活、对世界、对生命的关怀。 是从什么时候起,在小说创作中坚守独立的审美力量和形式价值,开始淡出作家们艺术探索的历程?就连很多曾经的“先锋作家”也接二连三地从这样的艺术命题中退场,降低了对生存和心灵追问的尺度和深度,“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披着“新写实主义”的外衣叙述生活的万千景象。小说的主题长期被寡淡而类同的现实奴役,看似在抒写生活的作品实际上是游离在现实的表层,这就致使文学出现虚浮的繁华,人们也因此一直对长篇小说怀有沉重的失望——关注现实确实拉近了与生活的距离,但却把阅读的想象都占为了它的殖民地。面对这种惨淡的景况,一个作家保持写作的责任和追问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尹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文本,他的长篇小说《童话》既完成了对生活内容的足够关照,又给物质之下人们空虚的精神和悬空的欲望以拯救和慰藉。这种不懈地而且具有一定深度地追问,使小说叙事在现实与想象中脱离单纯的场景和事件,表达出对生活、对世界、对生命的关怀。
《童话》是一部凝聚着勇气和理想的小说,其构造并阐述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排除了当下青春文学越来越缺乏生活经验的本质问题,通过对虚幻与现实的相互比照,描摹出一个高于实际生活的带有指导意义的“现实”,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和反观生活;二是探讨青春这个永恒的命题时不再使用既往陈旧浅泛的方式,而是运用时间的轮回,利用交叉的幻景使小说拥有“半面现实,半面虚景”的迷人色彩,最大化地创造、设想并享受生活。作为80后的年轻写作者,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带有理想色彩是理所当然的,但曾尹郁的这种理想是理性的产物,是写作者所要必备的一种“自省”的写作意识和态度。比如林晓白与曾默、林晓白与田田、曾默与张雨、曾默与胡香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他们而引串出的整个故事。虽然所有的细节和跌宕都不足为奇,但通过几个人物平常简约的生活内容,曾尹郁不但承担了描述的任务,更主要的是,直接拷问并戳穿小说依靠“生活花絮”获取生命力的神话,展示出一个和日常生活迥然相异的世界,触及青春时期特定的心理和处境意识,以相互的交叉点作为起点来透视这种生活方式和此种方式下这一群少年的情态。
针对“现实”这个问题,曾尹郁化用了类似“梦的解析”的哲学方式去显现。在《童话》的后半部分,林晓白所沉陷的生活被“梦”这把放大镜无穷地放大了,其开始与结束、跌宕与起伏都细致且真切,如同真实的生活任务和角色被他们承担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异常清晰的生活镜像。因此我要说,《童话》是在用一种“伪现实”的形式揭露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迷茫。
所以,《童话》是一部旗帜鲜明的先锋作品,矫正被一贯认为“青春是明媚而忧伤”的柔弱心态,进而追问这个时代生活的虚空和贫乏,富有力度地批评了人们沉醉于物质里而忽略内心情感的病态却成为一种常态的不自识。《童话》力图提醒人们告别这种危险的倾向,这也是我认为《童话》的核心是有关忏悔,有关信仰,有关生存的理由。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说,好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它应该联于这个世界隐秘的精神图景。是的,如果不能够挖掘出一种深度,那么这样的写作势必存在着“危险”——失却精神的作品是低劣的产品。我们所看到的《童话》不是沉醉于复制或套用可怜的生活经验,这是为了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更是为了让我们重新估价生活。
童话不是虚伪的幌子,童话是信仰的祈祷和羽化、心灵的抚慰、神圣的契约。当内心里惟一的对自我的信任也被偷换了概念,是《童话》依靠一种非正常状态的正常体验,准确地掂量出现实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