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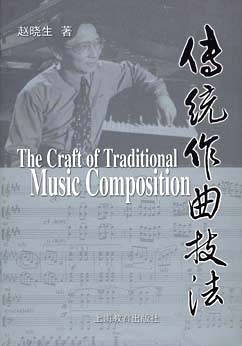 赵晓生,作曲家、钢琴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1981年至1984年,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钢琴艺术》杂志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现代音乐学会副会长和东方音乐协会、日本音乐研究会会员。 赵晓生,作曲家、钢琴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1981年至1984年,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钢琴艺术》杂志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现代音乐学会副会长和东方音乐协会、日本音乐研究会会员。
数十年来,赵晓生教授以其睿智的思维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厚的功力,在作曲理论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先后完成了“太极作曲系统”、“音集集合运动”、“音乐活性构造”作曲理论体系,为我国作曲理论的研究及作曲教学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多年的教学成果《传统作曲技法》于近日出版,为此,笔者走访了赵晓生教授。
梅雪林:赵教授,上海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您的力作《传统作曲技法》,首先表示祝贺。这本书的写作,前后共花去了十三年的时间,当中的甘苦太多,应该来说,这本书对于您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能谈谈写作这本书的情况吗?
赵晓生:此书从写第一页开始到今日“划上双纵线”,历时十三年。1985年从美国回来后,于1986年接手一个整班作曲学生,于是尝试全班上大课,做习题,模仿写作,命题写作等,萌发了写作“传统作曲技法”教程的想法。开始动笔在1989年,头两批上这门课的学生现已毕业多年且各有成就。转眼十七年过去,我教过的作曲学生“入室”上百,“俗家”成千。这里我只想提三位当年学这门课程的学生,安承弼,朝鲜族,现定居法国巴黎,每年均有委约创作,他先后得过国际作曲比赛的冠军(法国)、亚军(希腊)、季军(意大利),已很有名了。叶国辉,近年来不曾间断创作,在美国、台湾省等作曲比赛中获奖累累,并多次担任上海市政府委约创作。朱立熹,毕业后为越剧、沪剧、锡剧、评弹、粤剧等多种剧种创作戏曲音乐,成绩卓著,深受袁雪芬等老一辈艺术家及当今新秀们赏识。我提这几位学生是因为他们与本书写作有很大关系。他们是首批从旋律写作开始到写作“古组曲”、“奏鸣曲”一类习作的。可以说,本书中许多习题在给他们改题中产生。历时十三年,此书才杀青出版,我不禁想起为他们上课及倦缩在“独步斋”(由屋中心到四周墙壁皆为一步之遥)中书写最初几个章节的情形。书的写作实际分为两截,前一截从“绪论”到第六章第二节,起笔始于1991年12月27日(据爱妻生前日记记载),随后停笔十年之久,旧稿尽管封存多日,但经常被暗中复印传抄。正因为当年传抄部分手稿的学生推荐,上海教育出版社去年(2002年)与我签订合同,继续写作第六章第三节之后部分,时至今日(2003年7月)终于问世。
梅雪林:赵教授,您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写了这样一句令人感动的话:“谨将此书献给教会我知晓生命伟力的亲爱的妻。”能谈谈您的妻子吗?
赵晓生:2002年8月23日凌晨,《传统作曲技法》书稿全部完成,这一天对我本人有特殊意义。那天正好是我爱妻邓秀芝五十三周岁生日。历经一千零四十五个日日夜夜,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三次手术,六次化疗,但始终以最高昂的姿态,最乐观的心境,战胜来袭的疾病。在陪伴她治疗的过程中,我大彻大悟人生的真正价值。正是我的爱妻教我知晓生命之伟大力量,也正是她激励我在百忙中鸡鸣即起,子夜始息,完成本书的写作。由于这个原因,我特将本书献给我心爱的妻子作为生日礼物。待此书初校样送到我手中时,妻已病危。我日夜守候病榻边,趁护理空隙校对初样。这时,妻已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她骨瘦似柴,腹胀如鼓,滴水难咽,粒米不进,连吸入一口氧气也成为奢侈。但她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对抗病魔的无情侵噬。本书责任编辑梅雪林先生十分好意地做了一本“书型”,让她能有机会先期捧上我的新著,一本献给她的新著。然而,终于没能等到此书的正式出版,2003年3月17日14时41分,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此书写作过程与爱妻病情紧密相关。她的去世也显示了精神战胜躯体,爱情战胜癌魔,生命战胜死亡。因为,从纯医学角度衡量,她的生命已争得极大的延续。因而,她是胜利者,她高唱了一曲生命的凯歌。这就是我在题词中所说“教会我知晓生命伟力”的含义。
梅雪林:我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课程设置,均把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四大件”——和声、复调、配器、曲式,设为大课讲授、个别改题,而作为专业本体的作曲本身,却通常不设课程,只有“一对一”、“手把手”、“口传心授”式的改题。我们想知道是否完成了“四大件”的习题,学生就能作曲呢?作曲是否仅仅是“四大件”的总组装,而不具备其本身的特殊规律呢?作曲作为一门课程,能不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其基本规律呢?在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之前,学生是否需要经过必要的、合乎规律的训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