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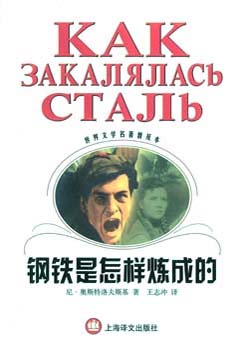 近几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连年畅销,稳踞不同排行榜,今年一开春,传媒又借央视黄金时段播中、乌合拍同名电视连续剧,掀起新一轮“钢铁热”的势头,再度把大众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本书上来。这不能不引起我如下的思考:它初次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国人正忙于开会,它成了那个年代的主流读物;现在,人们不怎么喜欢开会了,时间却更少了,因为在忙赚钱。可是,在老师和家长推荐给孩子们的书目里,在年轻人私下的谈论中,在出版社红红火火、稳中有升的印数上,《钢铁》的主流读物地位仍然稳稳当当,不可动摇。是什么引发了不同时代同种规模的群众性阅读?现代图书市场品种繁多,读者可选择的余地相当之大,又是什么导致了一本上一代人读过的旧书的再度风光,难道是“怀旧”使然?如果是,为什么出版社借势新出的同类旧书就没有这么火爆,甚至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近几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连年畅销,稳踞不同排行榜,今年一开春,传媒又借央视黄金时段播中、乌合拍同名电视连续剧,掀起新一轮“钢铁热”的势头,再度把大众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本书上来。这不能不引起我如下的思考:它初次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国人正忙于开会,它成了那个年代的主流读物;现在,人们不怎么喜欢开会了,时间却更少了,因为在忙赚钱。可是,在老师和家长推荐给孩子们的书目里,在年轻人私下的谈论中,在出版社红红火火、稳中有升的印数上,《钢铁》的主流读物地位仍然稳稳当当,不可动摇。是什么引发了不同时代同种规模的群众性阅读?现代图书市场品种繁多,读者可选择的余地相当之大,又是什么导致了一本上一代人读过的旧书的再度风光,难道是“怀旧”使然?如果是,为什么出版社借势新出的同类旧书就没有这么火爆,甚至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问题还是要回到这部书本身。我做过调查,《钢铁》的学生读者在回答有关“阅读动因”的询问时,常常选择“老师或家长推荐”这一条,但是老师和家长——或是笼统称为“别人”——推荐的图书肯定不止这一本,为什么被动接受阅读信息的人能够如此顺利而快捷地转变成主动阅读者呢?原因在于这本书确实有它独特而吸引人的地方。有趣的是,当问及“别人为什么推荐”时,答案一般是谈些比较宏大的理由:希望学会坚韧、顽强,能吃苦耐劳,等等,相当多的人们还提及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为主人公留下的那段闪光名言。可一旦问及“为什么喜欢”时,答案发生了十分感性而微妙的变化:它的艺术性、可读性,如此等等,最重要的地方,依年龄不同或直接或间接都提到了,那就是保尔和冬妮亚之间发生的故事,从相爱到割舍,都浪漫出一种力度:好起来,在小河边晒太阳同坐一辈子还嫌不够,坏起来扭头就走,多一眼都不看。是什么让他们爱得如此清澈,没有一点污染?
说句实话,这部书在中国之所以一向能得到广大年轻读者的青睐,确实是由于充盈在前半部里的关于成长的苦难和青涩又真实的爱情。在文学中没有爱情的时代,“冬妮亚”这三个字以它所特有的充满异国情调而又神秘温婉的意象搭配,温暖过多少渴望爱情的心灵,可以说,那时的“冬妮亚”就是“爱情”的代名词,“爱情”在读者心中随着少女冬妮亚的出现而滋长并辉煌一时,像冬日里一颗火烫火烫而又幽闭倨傲的孤星;又随着成年以后与保尔恩断情绝的冬妮亚,以别样的批评宣传模式在当年的读者心中泛起一样无望的涟漪——正是那样的时代暗合了美学意义上悲越凄绝的爱情,给了那一特定时代的年轻人一种“欲爱不能”的精神洗礼,从而深味了爱的崇高与难觅。
尽管这样的结局是凝重的,但第一代阅读《钢铁》的青年读者还是无比幸运地找到了可以现学现用的浪漫蓝本。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当时的另一些背景:在中国,千百年来一直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男女联姻的依据的,由于“五、四”运动的不彻底,就是到了标榜婚姻自主的民国时期,男女交往上的自由仍然局限在受过特定教育的小圈子里,构成都市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在“家”的樊笼里,能够娶朋友的妹妹做妻子,已经是很前卫的举动。这一点从现代文学家们给我们留下的大量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加上建国初期很多大龄干部进城,姑娘们不由分说就给组织上“安排”了,人生历程中多半永远失去了恋爱的季节,爱和被爱,再也无从找着感觉。有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保尔和冬妮亚一出现就成了众人追慕的“明星”,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人们实在是太需要爱的楷模了,哪怕模仿的只是表象、形式。所以男青年们纷纷吹着口哨敞着夹克衫双手插在裤兜里一个人出去转悠,像保尔那样;女青年们则悄悄迷恋小人书上画着的冬妮亚的蝴蝶结、遮阳帽以至后来的鬈发、高跟鞋和裙子上的花边,比照着打扮起来,到外面看书去。他们偷偷相会,尽量选择在有水的地方。虽然生活不单只凭相爱的热情,但相爱,使美好生活从此开始。
他们当然无法忘却这样一本为其人生发展带来重大启迪的好书,至于它的好处,当时的主流话语体系(也许还加上中国人固有的语言习惯)还不允许出现如上一些柔软的词汇,所以真正是“妙处难与君说”,真的要说起来,大伙就一块儿背诵那段闪闪发光的名言好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下,它的道德教化作用已经被无比地神圣化。只是诵读者心中止不住地会有一些“挟带”了“私货”的窃喜泛上来,泛上来,觉得窃火者的喜悦也不过如此。就这样,《钢铁》成了一个多重契合点,官方大张旗鼓的、温和的、以教化面目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悄悄的、开小差似的、初萌而无伤大雅的叛逆性心理,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一段融洽得近乎了不起的蜜月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