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奈尔对“19世纪观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们打开19世纪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几乎每一页的关键词都是“上等人”(gentlemen)——无论是对穷小子、富家女,还是律师、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个简洁直观、与阶层鲜明对应的标杆。千禧一代与此自动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同时掉进了新的、更为微妙的陷阱。在小镇的环境中,玛丽安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思维方式是绝对的少数派,同学们都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未来将不会局限在小镇里——他们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对玛丽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热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康奈尔甚至不敢邀请玛丽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可以轻易摒弃“19世纪的观念”,却无法拒绝周遭环境的共识;他不屑当个“上等人”,却必须假装做个跟伙伴们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比19世纪更19世纪。
一旦走出小镇的环境,成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权力关系立刻倒置。玛丽安所有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劣势都转化成了社交优势,她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使她具备迅速赶上大都市的时髦的资本(尽管她并不张扬这一点,甚至未必自知)。这一次陷入交往障碍、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尔。当然,我们从小说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玛丽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太多的快乐,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正如当年,带了别人去参加舞会的康奈尔,一点儿都不快乐。
在康奈尔和玛丽安约会的那栋来历不明的空置“鬼屋”里,他们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就这么空着,没人住,他说,要是卖不出去他们干嘛不把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诚地在问。
她耸耸肩。她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跟资本主义有关吧,她说。”
像资本主义之类久违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语焉不详的。模糊的概念总是包裹在一团潮湿的雾气中。如果我们拿鲁尼跟曾经同样以文坛天才少女的姿势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对鲁尼盛赞有加)相比,会发现后者带有明显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庞大芜杂,思维跳跃俏皮,注意给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肤色;她虽然乐于自嘲和反讽,但大体上愿意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看起来正在努力抹平差异、弥合创伤的世界。反观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鲁尼,她的笔触那么敏感、犀利,略带青涩却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好在还有真正的青春、成长的伤口、货真价实的荷尔蒙以及破茧重生的爱情(“他们像两株围绕着彼此生长的植物”)填满文本的空隙,让这部小说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没有被严肃的命题抽干一个好故事应有的湿度。当根据小说改编的剧集用耐心而稳定的近景、慢镜头张扬美好的身体时,你会觉得这画面本身的说服力胜过了大多数台词,你会相信惟有坦诚相见的肉身,才能与这个时常冷漠的世界抗衡。
萨莉·鲁尼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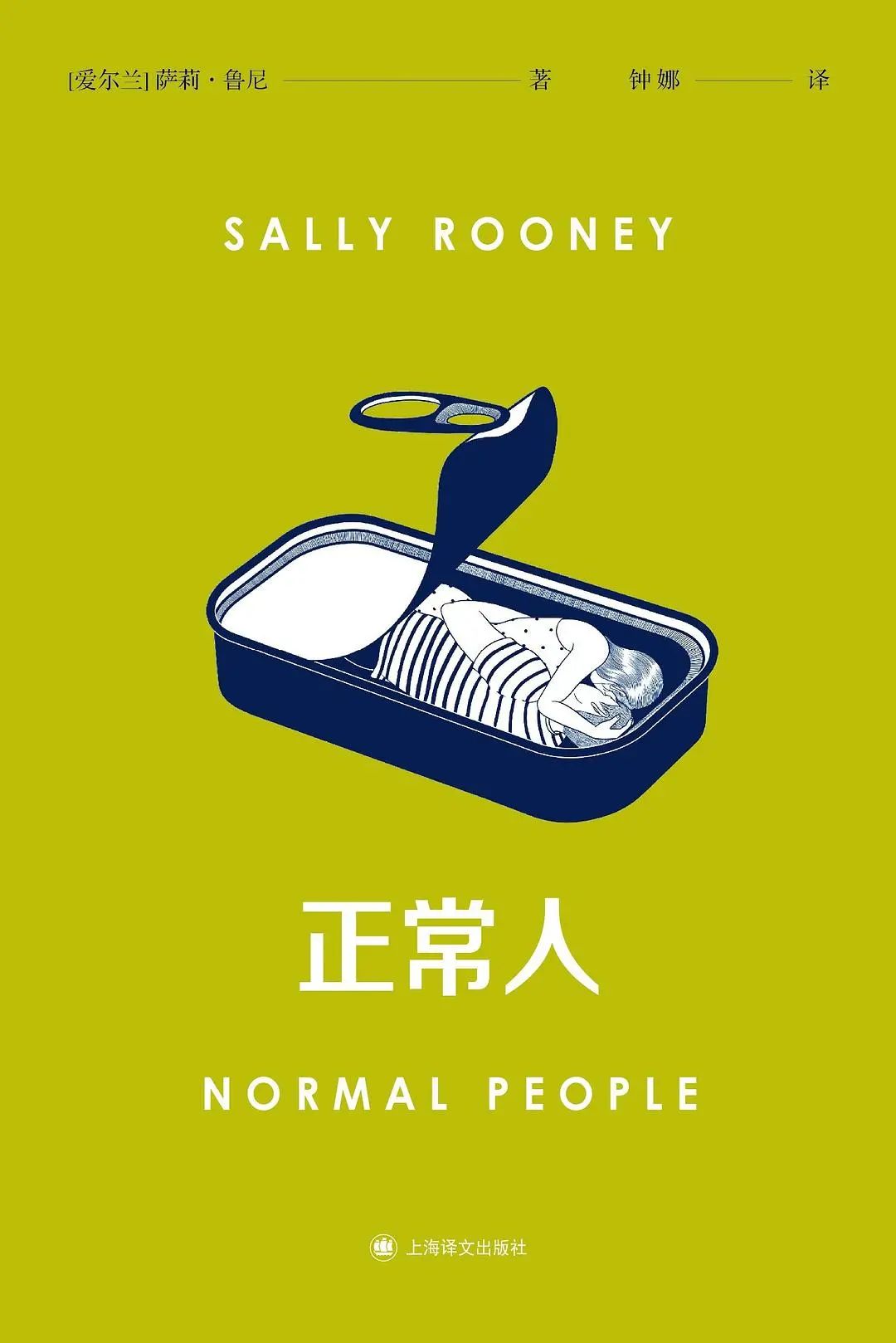
Normal People
《正常人》
[爱尔兰] 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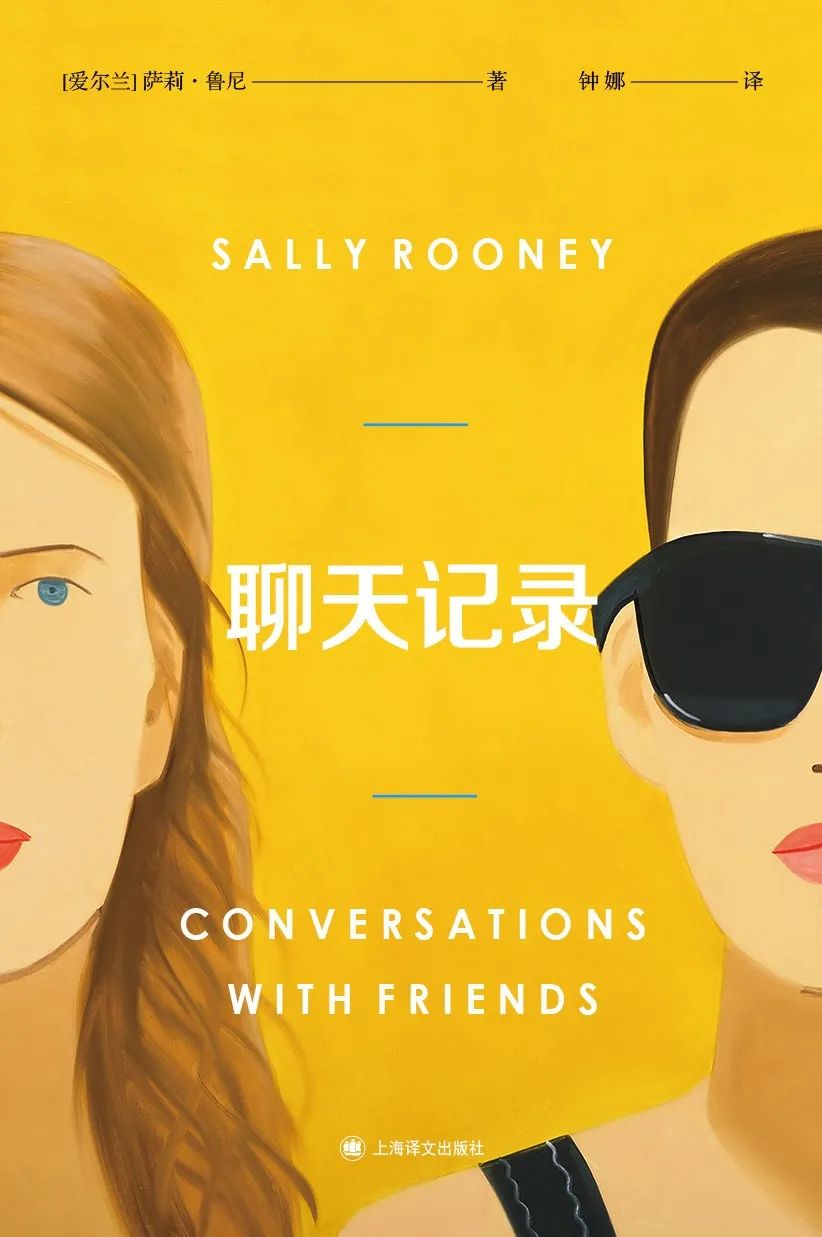
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
《聊天记录》
[爱尔兰] 萨莉·鲁尼 著
钟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