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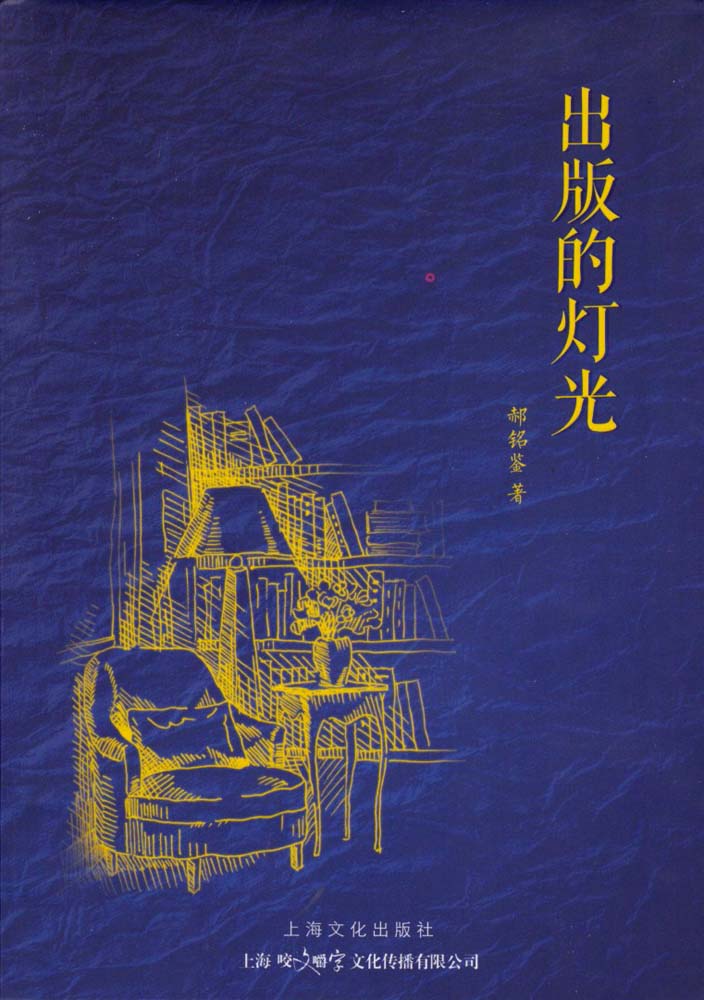 收于本书的文字,大部分刊于《编辑学刊》。该刊编辑不仅是“催生婆”,而且是“美容师”,为这些文字做了大量琐碎的工作,我很感激她们。《编辑学刊》创办三十年时,应约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现移作本书的代跋。 收于本书的文字,大部分刊于《编辑学刊》。该刊编辑不仅是“催生婆”,而且是“美容师”,为这些文字做了大量琐碎的工作,我很感激她们。《编辑学刊》创办三十年时,应约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现移作本书的代跋。
编辑是干什么的?有同行曾这样说:编辑犹如接力赛中的选手,从前边的人手中接过棒,然后撒腿向前奔去,把棒交给后边的人。对于期刊编辑来说,这一比喻尤为贴切。现在就来谈谈自己是怎么跑《编辑学刊》这一棒的。
2001年9月的一天,收到孙颙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说雷群明要到北美探亲,希望我挑起《编辑学刊》这副担子。孙颙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时,和我曾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升任新闻出版局局长以后,仍然经常回娘家看看,有事一般都是当面说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交代一下,很少用写信这种形式。这次郑重其事地写上一封信,我想是为了让我有个考虑的时间吧。
实话实说,我有点犹豫。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分身乏术。当时我是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也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还要兼任几个刊物的主编。特别是《咬文嚼字》创办不久,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二是心里犯怵。我和雷群明曾多次合作,深知他热爱出版工作,视编辑为太阳底下最好的职业,在主持《编辑学刊》时殚精竭虑,把刊物办到了相当的高度。谁来接这个刊物,都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然而,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没有退却的理由。孙颐几天后从昆明开会回来,在电话里问我考虑的结果,我的回答是:“试试看吧。”没想到一试就是十四年!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重千斤。”回看刚接手时的刊物,我能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手忙脚乱。匆匆搭建工作班子以后,便是心急火燎地组稿催稿。当时已是年底,雷群明处虽转来一些存稿,但我毕竟是个生手,心中没底。我曾在卷首语中用过一个标题——《凭“栏”翘首盼稿来》,由此可见惶惶不可终日的窘态。在这关键时刻,幸亏有各方援手。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编辑学会前会长、副会长刘杲、邵益文先生,感谢上海编辑学会老会长巢峰先生、上海出版协会前主席江曾培先生,感谢北京吴道弘、香港陈万雄、上海李伟国、江西朱胜龙诸位,他们以各种形式予刊物以支持,终于保证了刊物的顺利交接。
我国编辑出版类刊物为数并不多,屈指算来不过十家左右,但生存都比较艰难。我过去虽然也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但很少从刊物全局考虑问题。这次接手刊物以后,不能不想一想刊物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想一想期刊的现状和未来。我的前任王华良先生是一位学者,他主持的刊物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息;雷群明先生则是一位出版活动家,在出版界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办刊视野开阔,触角敏锐。我自忖缺乏他们二位的优势,只能从常规思路出发,集中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确认刊物的定位。编辑学刊编辑学刊,关键是两个字:一个是“编”,一个“学”。“编”既是本刊的读者对象,也是本刊的依靠力量。这个“编”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传统的图书编辑、期刊编辑,也包括报纸编辑、广电编辑、网络编辑,为此我们后来开辟了“传播前沿”一栏。“学”则体现了本刊的性质,同时也是评判本刊价值的依据。我们提出《编辑学刊》要成为“编辑学的理论高地,出版人的精神家园”,自觉为推动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次是巩固和发展刊物的个性。在全国编辑出版类刊物中,《编辑学刊》是一个老牌刊物,创刊伊始便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风采。和其他兄弟刊物相比,它不以传达出版政策见长,也不以报道编辑活动取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海派特点,能把理论探索和编辑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 会议间隙,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孙颙关心《编辑学刊》工作。立者为孙颙,坐者左为雷群明、右为郝铭鉴几位前任们的智慧结晶。在我接手后的几年中,力求巩固和发展这种特色。我们反复强调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贴近出版实践,希望刊物能与时俱进,无论是组建集团、“走出去”,还是数字出版、互联网十,都要及时提供深层次的思考;另一方面是提倡换副笔墨,本人习惯杂文思维,不喜欢堆砌术语,推崇《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幽灵”的比喻,推崇赫胥黎《物种起源》的“恺撒大帝”的开头,推崇朱光潜的一棵松树三种态度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刊物的风格。 再次是激发刊物的活力。一个刊物单靠红头文件是无法形成影响的,单靠经济补贴同样是无法持久生存的。刊物一定要有自身的造血能力,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为此,我们注重内外兼修。做编辑的,过去强调要坐得住,要有案头功夫;现在则不仅要坐得住,还要走得出。正是根据这一要求,我们建立了和出版界保持广泛联系的理事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举办了“智慧杯”征文大赛;和上海编辑学会联手,开设了名家荟萃的“海上人文讲坛”;利用到各地出差的机会,组织“专题圆桌会议”……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