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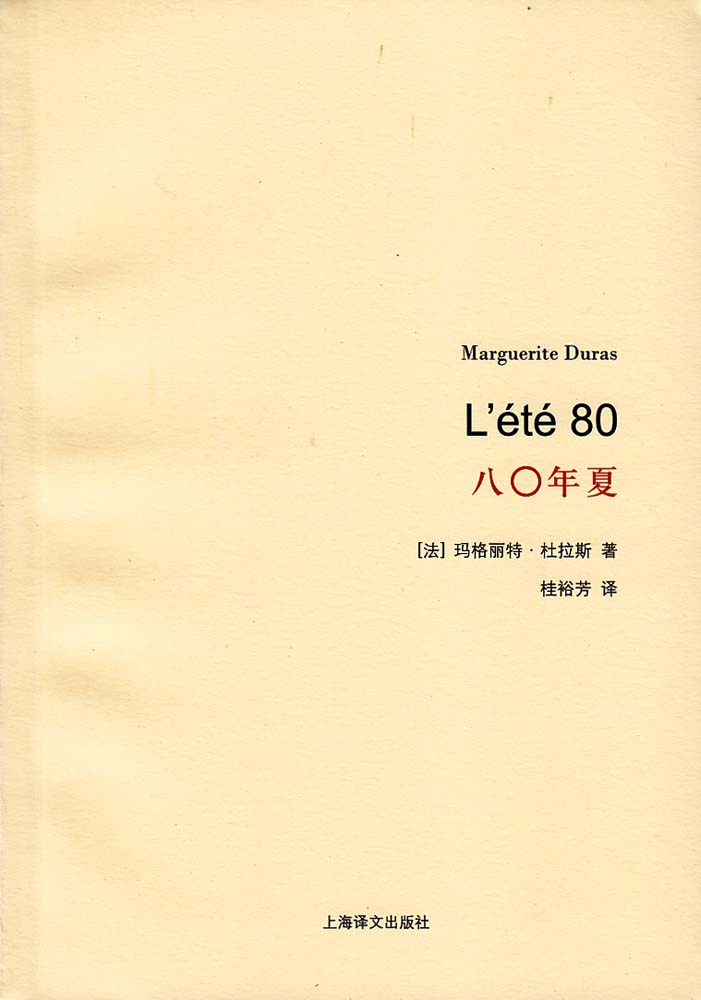 编者按 编者按
2014年11月27—3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大学、国际杜拉斯学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协办的“杜拉斯神话:跨越时空的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本文系法语文学翻译家黄荭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为:“百年诞辰:是谁误读了杜拉斯?”
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龚古尔奖失之交臂;1961年,《长别离》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4年,《劳儿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获戛纳电影节艺术和实验电影奖;1984年,《情人》荣膺龚古尔奖;1992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同名电影海报贴得满大街满世界都是,梁家辉和珍·玛琪演绎的情爱在欲望都市泛滥成灾,杜拉斯终于成了一个“通俗作家”……
盖棺论定?死亡会加快时间的筛选,要么被读者淡忘,要么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学记忆得以流传。随着2011年杜拉斯作品全集一二卷在“七星文库”出版,三四卷2014年面世,杜拉斯已然是端坐文学先贤祠的标准姿态:不朽。而随着百年诞辰的到来,国内外各种出版、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电影回顾展、戏剧演出更是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欢腾了得。
就中国的图书出版而言,上海译文出版社继续推进名家翻译杜拉斯系列,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蕾蒂西娅·塞纳克的《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黄荭译),并再版了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袁筱一译),阿兰·维尔贡德莱的《杜拉斯:穿越世纪》(胡小跃、郭欣译)也即将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至于“中国制造”,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李亚凡的《知性与叛逆:不可模仿的杜拉斯》,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凌小汐的《我们不能停止不爱:杜拉斯传》,世纪文睿推出我写的文集《杜拉斯的小音乐》。
从南到北,报刊媒体在四月份也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杜拉斯风”,《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文艺报》、《东方早报》、《社会科学报》、《外滩画报》、《东方卫报》、《南都周刊》、《深圳特区报》做了大大小小的杜拉斯专题,《经济观察报》、《上海壹周》、《南京晨报》、《晶报》、《广州文艺》、《长江商报》、《重庆日报》、《国际先驱导报》、《沈阳晚报》、《联合早报》、《齐鲁周刊》、《华西都市报》、《华夏时报》等北京和外省的报纸都或严肃或矫情地向法国女作家缅了怀致了敬。相对慢热的是学术界,截止到目前,只有《法国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术交流》、《名作欣赏》、《文学教育》、《电影文学》有论文发表。
从发表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来看,“情人”和“爱情”无疑是杜拉斯的关键词,加上“欲望”的发酵,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个中国文坛都在如痴如狂地爱着杜拉斯100岁“备受摧残”的容颜。
在今年四月初接受《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的采访时,我认为中国对杜拉斯的认识在三十载的阅读之后会逐渐走出“情人现象”,事实证明,我是过于乐观了。《情人》成了杜拉斯的魔咒,谁能唤醒森林里的“睡美人”?中国媒体对杜拉斯的总体印象还是浮浅的,跳不出白人小女孩十五岁半的“爱情”,把杜拉斯一生的创作跟《情人》画上等号显然是过于天真和轻率了。
在《驳圣伯夫》中,普鲁斯特很清醒地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这种说法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在日常生活状态下,人们是那么容易忽略那‘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人们常常搞不清楚哪个‘自我’是‘日常自我’,哪个‘自我’是‘作者自我’,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日常视角’去分析和判断一个作者的创作秘密,因为角度的错误,所以人们才会有日常层面的对作者的无尽苛责或纵容。”
杜拉斯动不动挂在嘴边的话是:“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字里。”文字呈现的“自我”和“作家自我”是有距离的,这也是真实和“神话”的距离,而杜拉斯最擅长的就是把这种距离模糊化。从古至今,作家的存在=作品的存在,作品活得比作者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迁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中也说过,“一代代读者重新创造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使其历久弥新。书本的白纸黑字因此便如同乐谱,本身并非音乐,但当音乐家演奏——或者如大家所说的‘诠释’——它时,便成为音乐。阅读文本就像同时演奏并聆听音乐,读者自己变成了诠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