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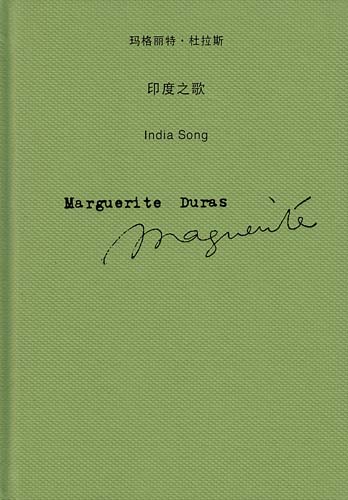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情人》(L’Amant)一书被王道乾先生译介到中国,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为万千中国读者所推崇,影响了一些先锋作家的创作风格,并成为持久风尚。对很多人而言,杜拉斯是《情人》的作者,《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的编剧,是在少女时代与中国情人有过刻骨情爱的传奇女性,是绘尽情色之美的时尚标签。但在成为“现象”之前,杜拉斯其实已走过文学生涯和人生的大半程,与在中国被“神化”相比,杜拉斯在其母国的“际遇”更加复杂,其文学创作也仅非一部《情人》可以概括。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情人》(L’Amant)一书被王道乾先生译介到中国,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为万千中国读者所推崇,影响了一些先锋作家的创作风格,并成为持久风尚。对很多人而言,杜拉斯是《情人》的作者,《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的编剧,是在少女时代与中国情人有过刻骨情爱的传奇女性,是绘尽情色之美的时尚标签。但在成为“现象”之前,杜拉斯其实已走过文学生涯和人生的大半程,与在中国被“神化”相比,杜拉斯在其母国的“际遇”更加复杂,其文学创作也仅非一部《情人》可以概括。
杜拉斯在法国
1984年,具有自传色彩的《情人》荣膺龚古尔大奖,畅销不衰,轰动法国并获得世界性声誉,当时杜拉斯已有70岁。贯以提携新秀为宗旨的龚古尔奖为杜拉斯颁发了这份特别的“终身成就奖”。在此之前,这位多产的女作家虽然凭借《抵挡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和《副领事》(Le Vice-Consul )等受到瞩目,但其风格自成一派,难以归类,不在主流之列,仅限于学术圈研究,不为大众所熟知,即便在文学界也一直是争议与戏谑的对象。有人挖苦她的作品只是“改良后的言情小说”,说她本人是“在密特朗扶持下故作深沉的平庸又自负的女人”。与杜拉斯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法兰西学术院第一位女院士)亦曾取笑杜拉斯的《广岛之恋》:“为何不说‘奥斯维辛我的亲’(Auschwitz mon chou)?”杜拉斯是著名作家莫里斯·布朗肖、诗人兼画家亨利·米修和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等人的好友,但与萨特和波伏娃并不十分投缘。她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什么都喜欢接触,什么都要评论一番:文学、电影、政治、花边新闻、甚至足球。她参加过二战时的抵抗运动,随后又加入了共产党(1955年脱离共产党)。她曾参与1968年五月风暴,后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亦对左派政府大加点评,在文学界和政界都树敌颇多,褒贬不一。总之,一说起杜拉斯,不论其人还是作品,往往能引发分裂与激辩。正如本文标题套用与杜拉斯同时代的法国女作家萨冈的《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书名一般,爱者为之倾倒,如同无法戒掉的瘾;憎者则对其全然否定,极力讽刺。
无论人们喜欢或是厌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法国乃至全世界,杜拉斯热从未减退。女作家身后得到的评价多为肯定与称颂,其创作风格为许多作家带来灵感,如克丽丝蒂娜·昂戈和阿妮·艾尔诺。作家兼记者弗朗索瓦斯·吉鲁的一句话极为中肯:“人们一直嘲讽她、戏拟她的作品,但从未及得上她。”其实如此频繁地被戏拟又何尝不可理解为某种致敬?在她去世后仅仅15年,作品就被纳入法国伽利马出版社赫赫有名的七星文库系列,该系列专门收录经典作家作品,位列其中意味着已进入文学的万神殿。2014年,时值杜拉斯百年诞辰,十余部戏剧在法国轮番上演,其中在巴黎上演的《广场》《萨瓦纳湾》以及《玛格丽特与总统》三部曲分别对应杜拉斯的“三段年华”,导演迪迪埃·贝萨斯这样评述杜拉斯:“她一直在说自己,即便是通过她所创造的人物。但她拥有这样的天赋,在谈论她自己的时候,也是在谈论我们。”这或许就是杜拉斯能够激发许多人共鸣的原因。在看似斑斓流动、变化迭出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独属于她的韵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