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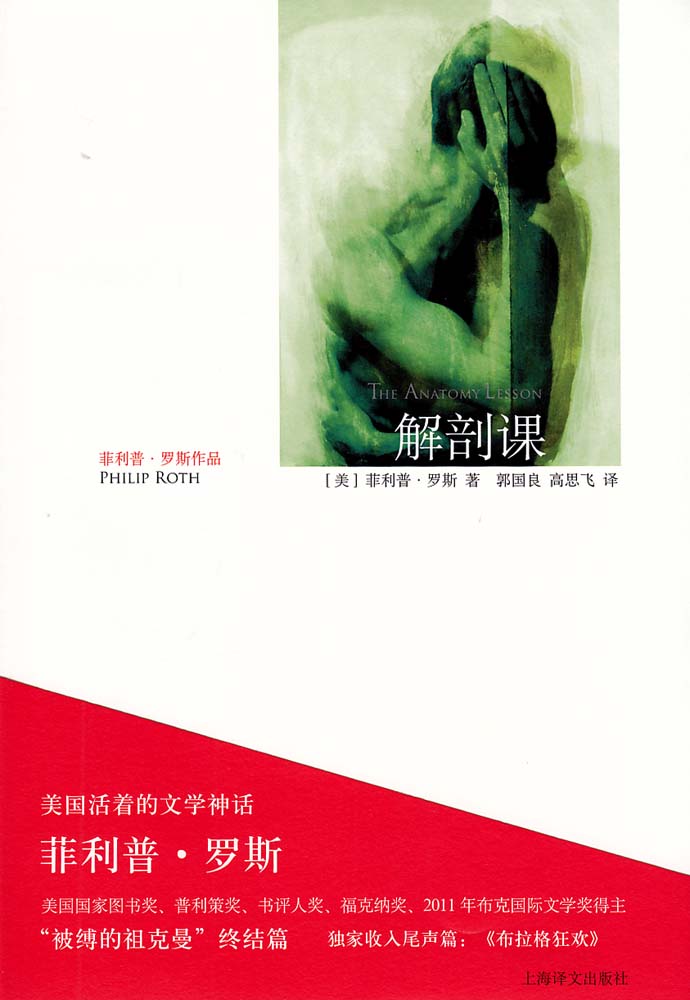 读罗斯的小说,在那花团锦簇、结构繁复、层层叠叠的反讽、自嘲、怨怼、忏悔和揶揄中,你最后听到的,终是一声叹息的无奈 读罗斯的小说,在那花团锦簇、结构繁复、层层叠叠的反讽、自嘲、怨怼、忏悔和揶揄中,你最后听到的,终是一声叹息的无奈
在菲利普·罗斯以“祖克曼”、“凯普什”等主人公为题的系列小说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人物都有他本人的影子。换句话说,罗斯的“他我”以不同程度的自传色彩勾织起了作家的成长经历。但小说体裁的虚构本质又决定了这种自传性是很可疑的,特别是,当作者发现一些以他自己名义未必方便探讨的议题和观点,可换种方式由他笔下的虚构人物去探讨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作者本人和虚构人物之间画等号呢?稍具一些小说阅读常识的读者会谨慎地打上一个问号,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在作者和人物之间画等号真是太具有诱惑力了。
《被释放的祖克曼》是罗斯“被束缚的祖克曼”三部曲的第二部。所谓“被束缚”,即是主人公兼作家祖克曼被他所虚构的故事绑架而不得解脱。听上去很魔幻?罗斯证明了这种魔幻是多么致命。在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鬼作家》中,23岁的祖克曼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因牵扯犹太民族问题而触怒家乡父老,以至年轻作家与父亲彻底决裂。显然,用艺术与生活、虚构与真实之类的话语“教育”犹太父老,万万敌不过后者在艰难岁月中对不安全处境节节攀升的恐惧,而祖克曼尽管从人性而非民族性角度揭露家族的不光彩内幕,还是给犹太人在异地求生的努力浇了一盆因为无心所以更见残忍的冷水。
因而,我们只有理解了那一代犹太人的爱憎,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祖克曼的困境。如果说这种困境在《鬼作家》中表现为犹太人身份认同这一较为单一的主题,那么,在第二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这种困境的广度和深度均被大大拓展了。《鬼作家》中20世纪50年代的犹太人社区,转眼变成了1969年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民权运动蜂起、冷战越战反战交相辉映、女权和性革命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祖克曼出版了令他大红大紫的“色情”小说《卡诺夫斯基》(是年罗斯出版《波特诺伊的怨诉》,也是一本尺度很大的小说),收入“比他过去三十年任何一年多九十八万五千美元”。
祖克曼的成功在于与时代风潮的巧合,有人赞美他解放了“力比多”,有人感谢他代言了他们的心声,还有女粉丝邀他同赴意大利滚床单……但就如这些不请自来的高帽子,时代风潮又反过来对他提出要求,既然你如此有名(还如此有钱),那么就请你在反战宣言上签字,为弱势族群呐喊,为异议分子助威,为锒铛入狱的进步人士鸣不平……罗斯深知,当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将一顶无懈可击的冠冕强加到人身上时,所产生的负面性远大于它本来所要反对的东西,甚至,还大大损害了它所欲维护的那些东西。而那种媚俗、那种诳言,将与艺术和生活中所有有生命力的东西背道而驰,你将一刻不停地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写“正确”的书。因此,祖克曼说自己配不上为某某签字呐喊助威鸣不平的“圣女”妻子,这既是实话,也是反话。也因此,《鬼作家》中罗斯虚构的《安妮日记》的作者会选择隐姓埋名的“死亡”,而不是顶着沉重的荣誉光环“生还”,后者实在要比集中营中的生活更能把人杀死。
虚构与现实之间原本微妙的平衡关系由此被打破,并由前者侵入后者而成为祖克曼无法释怀的噩梦,从这一刻起,这本讲述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的小说变得既混乱又荒谬,既可笑又可悲了。有意思的是,罗斯借祖克曼之口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在后者看来,“悲剧通过把情感推向极致而耗尽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喜剧则靠着把那些当了真就很荒谬的事情模仿出来而给观众一种轻松愉悦的心境”,然而,“亚里士多德让我很失望,他对荒诞剧只字未提,而我正是这剧中的主角。”荒诞剧的另一名称其实可叫作“悲喜剧”,祖克曼的“悲喜剧”就在于他的生活成了不受他掌控的大众想象力的来源,更在于他不愿顺势为这熊熊燃烧的想象力再添一把火(迥异于如今不惜各种绯闻但求曝光率的那些名人),罗斯因之称他是一个问题扎堆的国家的一个问题扎堆的作家。话说回来,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你在追随祖克曼故事的同时观照现实,发现现实中处处存在令人泪奔也连带碰触到笑点的时刻,而这就是生活亘古不变的本质。
罗斯最后为祖克曼打造了一个看似乌托邦的结局:他被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乡缠上,好不容易将之踢掉又接到匿名绑架电话,原以为母亲遭了殃,结果是父亲弥留,而这个父亲憋足最后一口气就为骂他一声“杂种”,原来父亲一直念念不忘儿子对犹太人的“污蔑”……这下好了,可以一口气干掉乡情、亲情、人情、友情,特别是让他纠结半生的父亲。小说结尾,一身轻松的祖克曼再也不需要做一只“躲在无辜教授眼镜背后的狡猾小狐狸”,而可以做回把心爱的女孩摁在地板上而不必无聊地扯上半天克尔恺郭尔的生猛情人了——但问题又来了,“你不再是任何人的儿子,你不再是某个好女人的丈夫,你不再是你弟弟的哥哥,你不再有故乡”,那么,你究竟是谁?你还有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