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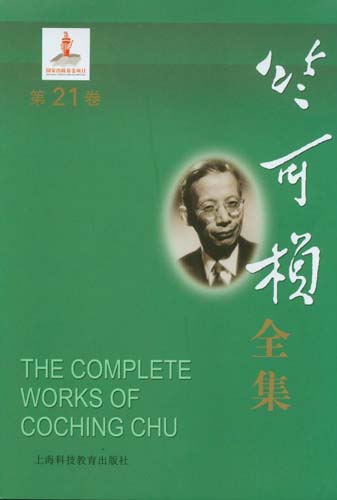 1958年春,竺可桢赴广州参加广东科学馆开幕典礼及广东省科研规划(1958-1962)会议。会议间歇,竺可桢去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 1958年春,竺可桢赴广州参加广东科学馆开幕典礼及广东省科研规划(1958-1962)会议。会议间歇,竺可桢去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
十点至河南中山大学钟楼对面晤陈寅恪,他精神和去年相似,惟稍胖。我约其十二月去京参加学部委﹝员﹞会,他说他不耐开会,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云云。他对于仲揆、孟和统问到了。至楼下,杨秘书为我们拍一照。寅恪夫人说我们是五十年前在复旦同桌读书的人。次晤姜立夫,他精神比去年好,也愿于政协开会时去北京,他与陈省身也久未通讯云。十二点半回。(《竺可桢日记》第十卷,1958年4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五卷79页)
陈寅恪失明之后仍然勤于著述,业余娱乐唯有听听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享誉中外,但陈寅恪却喜欢听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演唱。1952年,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壬辰广州元夕收音机中听张君秋唱祭塔”。陈寅恪仅是在收音机中聆听,身居京城的竺可桢则“近水楼台先得月”,1957年元旦:“晚七点至怀仁堂〔集〕会拜年,毛主席、刘委员长、朱副主席统到,遇聂副总理。七点半看京剧晚会,有李多奎《钓金龟》,张君秋(起白娘娘)《祭塔》,谭富英、裘盛戎《捉放曹》,马连良《失印救火》(《胭脂宝褶》中一折),统唱得很精彩。”(《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7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491页)1960年,张君秋南下广州演戏,陈寅恪为此又赋诗一首“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诗”。这些记载或可为陈寅恪对竺可桢所说“但﹝愿﹞到京听戏,不是听梅兰芳,而是听张君秋”添一解。
1961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及海南岛出席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会议,百忙之中,他仍然不忘老友陈寅恪嘱托之事,在日记中记道:
谢三宾,《一笑堂诗集》,陈寅恪要,要抄一份,北京图书馆。(《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1年1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17页)
《一笑堂集》是晚明谢三宾诗集,刻于康熙年间,既不收于《四库全书》,也不见于《中国丛书综录》。此类罕见书,陈寅恪亦唯有拜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这位老友,方有能力从北京图书馆借抄一份。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其宗旨是阐发“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反清复明的事迹,“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间要阅读大量明末清初士人之著作,而作为降清人士谢三宾的《一笑堂集》自然亦在参考书之一。
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1953年曾赴北京,拜访文史专家邓之诚,为其昔年所作画卷《旧京春色》求邓题词。其间,冼玉清向喜欢藏书的邓之诚通报了一些古籍聚散消息:“冼(玉清)托人取手卷去,并告知:伦哲如卖与北京图书馆之书,有李驎《虬峰文集》二十卷,谢三宾《一笑堂集》四卷,沈寿民《姑山遗集》三十卷,杜登春《尺五楼诗》九卷,周在浚《黎庄集》二卷,皆亟欲一见者,当谋借钞之。”(《邓之诚日记》第6册第361页,1953年9月27日[阴历八月二十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书的伦哲如果然是大藏书家,晚年散出的古籍皆是罕见之书。冼玉清是陈寅恪暮年的挚友,估计是她向陈寅恪提供了谢三宾《一笑堂集》被收藏的所在。
1962年2月竺可桢赴广州参加科学技术十年(1963-1972)规划会议。会议开幕之前,竺可桢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去看望陈寅恪:
晨六点起,做太极拳。早餐后九点半,至河南区中山大学办公室,先由陈序经招待,通知我和吴﹝副﹞院长所要看的人,即陈寅恪和姜立夫。时去看中大物理系、生物系的人已有不少在等着。我和刘力、吴副院长乃去看寅恪。他住原住的宿舍二楼,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吴副院长与彼乃25年前联大老同事,与其夫人亦相稔。谈及供应,说广东供应虽好,但为了北京和各方来人多也穷于应付。粤省对华侨为了赚外汇亦特别优待。谈到英国,云人只知英国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的汉简,而不知Aurel Stein初发现莫高窟时取了许﹝多﹞藏文的稿件,对于唐和吐蕃史料尤可宝贵。其初存于Indian Office,现不知在何处。曾函科学院图书馆,但迄无回信(云已去函二年,其夫人唐君不知其事)。我允回京后为之一查。又谈及今年壬寅,据印度历乃是大灾年。中国相传“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今年阴历年初是立春(晦日),而岁逢摄提格,是宋以来第一次(据我估计大约450年一次)。日月合璧无疑是有的,但五星连珠则未必,盖金木水火土聚于一宿(中国宿又大小不同)乃要数万年才有一次。(《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2年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200-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