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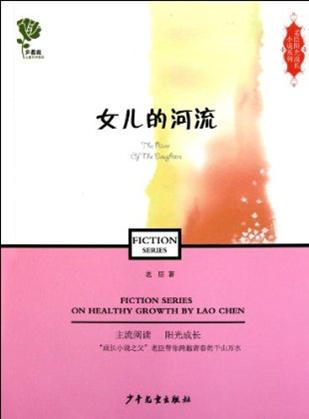 阅读老臣的小说,有一种久违的气息。这种独特的气息属于那个崇尚艺术探索、崇尚文学介入生活的时代,也是我们今天丢失(至少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的宝贵的精神之一。 阅读老臣的小说,有一种久违的气息。这种独特的气息属于那个崇尚艺术探索、崇尚文学介入生活的时代,也是我们今天丢失(至少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的宝贵的精神之一。
老臣虽然不老,但是写小说却很有些年头了。他那些充满探索意识和个性色彩的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在当代儿童文学的探索之路上,这些小说是一道重要的风景。关于他的创作成就以及特色,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述。但是在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作品?它们和现在正畅销的青春文学有什么不同的气质和追求?对于现在的少年文学创作,它们能给予一些什么样的补充?
老臣的很多小说,在最初发表的那个时候,是被称作“少年小说”的。而现在,我们习惯称之为“成长小说”。关于“成长小说”的概念和内涵,虽然多有讨论,非但越辩越明晰,反而越来越宽泛,大约所有的儿童小说称作“成长小说”都不会错。但是,老臣的小说确有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的内核——精神的蜕变。他那些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像《窗外是海》《泡沫》《盲琴》《窑口有棵树》《十六岁诗人的远方》等等,主人公在经历了一场非凡事件之后,度过生命中的某一个节点,内心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激荡,对于自身、生命和他人的认识,都抵达了不同的境界。
然而,这个节点往往非常残酷,甚至伴随着死亡。老臣的大多数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往往都以辽西的山村或者辽东的菊花岛为背景,他对于故乡有着浓烈的感情,这感情包含着眷恋,同时也有浓浓的悲哀和深刻反思。这让老臣的小说不那么轻盈,故乡土地以及他对苦难与生命的敏感与思考,都无法让他轻盈,更不能轻飘。乡间的生活自然有许多趣事,但对于老臣来说,人们正在经历的物质贫困和精神困境、少年人在成长之路上的内心搏斗、生命应该怎么度过,等等,这些深重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内心。和自然搏斗的生活给了这里的人们强韧的生命力,给了他们勤劳朴实忍耐的性格,也给了他们强烈的冲出去的欲望,但是,生活本身的残酷以及在少年中沿袭的残忍游戏,也使得少年们不得不经受沉重的“成人礼”。“我们”在二炮的带领下最终导致了伙伴哑巴三儿的死亡(《泡沫》);在琴师到来之前,身患绝症的定子其乐趣却在于折磨伙伴假丫头;亮光的爷爷和父亲的生命与健康都被矿窑微薄的酬劳剥夺,但是少年亮光却要以牺牲尊严为代价,忍受窑主高高在上的施舍(《尊严》)……然而,这却是一片并没有让人绝望的土地。悲剧引起的不是人的毁灭,而是人性内在的强力与善良的凝聚,这种向上的倔强的力量像是暴风雨之后的阳光,格外耀眼。或许也是这样的原因,老臣的这套新文集叫做“阳光成长小说系列”。显然,这阳光照耀在暴风雨之后。
《男儿身上三盏灯》《开往秋天的地铁》《图苏拉冰川》《风中的额济纳》《月光的价钱》等篇章,是老臣的新作。这些小说要明媚得多。最初的那些成长小说中,老臣不但是讲述者,也是参与者,他的内心和精神与笔下的少年主人公融为一体,同起同落,并非过来人的指点和隔岸观火,而是一同困惑、挣扎、奋起。能够感觉出,每结束一篇小说,都仿佛结束一场战斗,完成一次精神上的拷问,在那些凝练到紧张的字里行间,能感觉到老臣气喘吁吁的搏斗。那些小说如此重,压得老臣喘不过气来。在创作那些小说期间,我想,老臣自己也处在一个成长期。
而这些新作中的主人公虽然也正在努力攀过某道“坎儿”,有的是因为幼年留下阴影而惧怕黑暗(《男儿身上三盏灯》),有的是寻找消失在沙漠中的父亲(《风中的额济纳》),或者“第一次出门”的意外遭遇(《开往秋天的地铁》)……然而,这时候的老臣,或许是因为已经做了父亲,他变得从容而超脱,这些作品中,一眼能够看出有一个“长辈”的观照。作者老臣已经掌控了主人公的命运,他的心境、对世界的认知已经和主人公相分别,含着爱抚的、鼓励的目光,注视着或者暗中指点着少年们外出历练。这些小说拓宽了生活的空间,竭力避免儿童文学中生活被“窄化”的倾向,增加了少年和这个世界的接触点。
文学的诸多功能里,在青春文学里可能过滤得只剩下了抚慰,虽然这也非常重要,但毕竟是贫乏的。我总在盼望,能有什么样的契机,让老臣的小说,以及更多不同面貌的小说,走进当下少年的阅读生活。每一种写作都有它的不可替代性,我们不是要以这些小说取代轻松幽默、时尚娱乐以及自恋颓废的作品,但是希望文学创作和阅读都能够保持它的丰富性,不要冷落有难度的写作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