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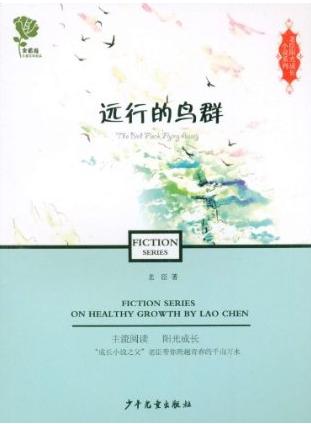 老臣:感谢《儿童文学选刊》为我们提供这次对话的机会。按照批评界的分类,我们的对话似乎有第四、第五代作家面对的含义。中国的儿童文学、少儿小说,经过几代作家的开拓、探索、实践,快走完90年代,快走入21世纪,目前的确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 老臣:感谢《儿童文学选刊》为我们提供这次对话的机会。按照批评界的分类,我们的对话似乎有第四、第五代作家面对的含义。中国的儿童文学、少儿小说,经过几代作家的开拓、探索、实践,快走完90年代,快走入21世纪,目前的确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
梅子涵:世纪的划定原本是一种人为的事,没有“必然性”,但是利用这种划定来进行总结和预设,却是习惯成自然,人类总不放过。那么你所说的这个“时间”的“很有意义”,其中的相当的意义可能就是会用来作总结和预设。当然在这里,我们是没有篇幅来总结和预设的。我们只是“双人茶座”里的小谈,小谈谈。
老:谈谈你的作品。
梅:主要谈谈你的作品。同时谈谈第五代和别的。
老:我这几年一直在做生意,同时也一直在写少儿小说。因为我喜欢写作,喜欢写少儿小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梅:对你的小说我是一直很注意和喜欢的。几年前,我为明天出版社主编《当代创意性儿童小说选》时不是就选了你的《夜道》和《窗处是海》吗?我不知道你写它们时是不是已经做生意了,但是它们给人的感觉是来自一种宁静的心情。
我在读《夜道》和《窗处是海》时,心里就有过很确切的震动。感到了比我们年轻的青年作家的艺术性和实力。我把你看成他们的代表之一,在我想着这一点的时候,当然脑子里也叠印着彭学军、曾小春他们。
我现在不用翻书,还能很完整地讲出那两个故事。一个儿子和他的后爹的故事,一个爷爷和他的孙子的故事。一个故事发生在夜道的小驴车上,一个发生在海边,发生在海边小屋窗口的“视角”里……它们给了我不同的感动又是多方面的:人性的闪亮和温暖;叙述和语言都相当精致——看得到的练就;也有那么一点幽默——它们不是毕露的,而是偶尔地表现在一首歌里和一声陡然的大喊里……
老:但是你是不是认为在“第五代”的小说里,更多的是沉郁、凝重和老气横秋?
梅:不一定说他们都这样,而是一部分吧,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几位比较醒目者吧。曾小春对我说过,他的生活背景和感觉就是这样的,难于轻松和幽默。彭学军说,她并没有专门的想过,给儿童的文学应该怎样写。这就是说,他们比较从自我出发。
我也想这样理解,他们走入儿童文学,开始为儿童写作,他们的意识里都是有着对于以前的“小儿科”儿童文学的抗拒的。他们不想写那样的儿童文学和小说,而是想走一条自己的文学的路。就走成了这样。我以前也是过样想的,现在也继续在这样走,只不过具体的认识和操作不一样些。但是我认为我和他们,他们和我,有着很本质的相似之处。
老:这种沉郁、凝重、没有轻松和幽默,已经引起了批评界的非议,他们称是成人化倾向。
梅:称它们是成人化倾向科学吗?如果说科学的话,那就是说,成人,成人的文学就是沉郁的,就是凝重的,没有轻松,没有幽默。然而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真正的喜剧和快乐正是来自为成人写的文学戏剧、电影、漫画……
在儿童文学里,“成人化倾向”的说法常常是在乱用,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标准。叙事的标准,语言的标准,故事的标准,主题深度的标准……没有建立,而是似是而非,悖论重重,实在经不起盘问和推敲。
同样的道理,沉郁和凝重之类,也未必只能是成人的文学所独有。它们作为一种可能在儿童文学里是一直有的。例如安徒生的某些童话和叶圣陶的稻草人的故事。它们也是一种审美。它们有它们的叙事和情绪。美学的范围对儿童文学也应该是开阔的。我们不要只讲快乐和游戏,儿童文学的读者既然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多层面的组合,那么难道他们的审美会不是多层面的吗?我们不要喜欢去制定单一,我们要允许丰富。我最近在《文艺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返归”儿童文学,提出我认为的的确存在一种真正叫做儿童文学的文学,其意思不是说儿童文学只能幽默、快活之类,我在这里特地想打个招呼。
老:是否因为你近期的写作是处在一种幽默和快活的状态?
梅:有一点的。我想一个既具有理论状态又具有创作状态的人,尤其不能犯片面性,以他的状态来制定状态。
老:但是你近期的幽默、快活状态的确很引人注目和受到读者的欣赏啊,我们也都在谈论和表示欣赏。儿童文学界也总是更看重轻松和快乐的。
梅:我认为我们也必须承认看重的理由。谁喜欢一天到晚沉郁、凝重?沉郁、凝重的人也不喜欢。沉郁、凝重的人也想摆脱的。但是生活要让他们沉郁和凝重。尤碁 是不成熟的、处在孩子状态的那一部分儿童,年龄小一些的那些儿童,贾里和贾梅们,比贾里和贾梅们更小的那一些。所以《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实际上是以虚构的贾里贾梅去适合真实的贾里贾梅们。真实的喜欢轻松和快乐的贾里贾梅们是一个众多的数字。看重轻松和快乐正是看重这种适合。看重它们的确为阅读、为生活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但是“适合”并不是唯一的。“适合大多数”不是唯一的。我一直这样认为。文学创作里总会出现“少数人的美学”。作家自己认为的可能性,他的兴趣和追求,他的情绪和语言,他的某一个时间里的认识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