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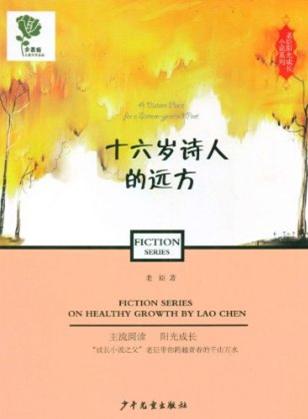 “其实儿童小说很难写”,但这话至今还有好些人不以为然。为什么,简而言之,因为他们没看到或者不承认少年儿童也有个不同于成人的心灵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层次复杂,变幻多端,差异微妙,难以把握。而把儿童小说的艺术性已看成老奶奶讲故事,说得有头有尾、善恶分明就可以了。显然这是对儿童小说的一种误解,一种虽无贬义却是愚昧的、危害很大的误解。当代儿童小说(特别是少年小说)正以自己的实践扭转着这种谬误,让儿童小说真正地成为儿童少年心灵的艺术品。陈玉彬(老臣)就是这种儿童小说观的儿童文学作家。 “其实儿童小说很难写”,但这话至今还有好些人不以为然。为什么,简而言之,因为他们没看到或者不承认少年儿童也有个不同于成人的心灵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层次复杂,变幻多端,差异微妙,难以把握。而把儿童小说的艺术性已看成老奶奶讲故事,说得有头有尾、善恶分明就可以了。显然这是对儿童小说的一种误解,一种虽无贬义却是愚昧的、危害很大的误解。当代儿童小说(特别是少年小说)正以自己的实践扭转着这种谬误,让儿童小说真正地成为儿童少年心灵的艺术品。陈玉彬(老臣)就是这种儿童小说观的儿童文学作家。
从90年代开始,陈玉彬从事少年小说创作,数来也有几年了。期间,全国重点的儿童文学刊物,几乎家家都以头题发表过他的作品,把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辽西生活展示经全国的少年读者,让他们结识形形色色的辽西少年形象和他们朴实强悍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各自境遇里所表现也的优秀品质。
辽西少年,他们也和各地的少年儿童一样,有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生活的欢快和幸福,同时也面临困境,特别在辽西山区,要面对贫困、面对失学、面对父母和家庭的不幸、面对旧传统、面对新型社会的经济关系与人际关系等等。应当说当今现实摆在社会面前的许多问题毫无隐蔽的也摆在少年儿童面前了。他们无法躲避,无处躲避,现实的复杂多变,要比六七十年代严重得多。许多的家长和老师已经看到,当今的中国少年儿童,虽说被溺爱地称为“小太阳”,但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活的很累、很苦,特别在农村,在学的很累、很苦,不在学的更累、更苦,他们必须投入生活(虽然他们并不咋明白生活的真谛),不但要受肌体之苦,还要受精神折磨。
比如《窑口有棵树》中的明震,为能交上读书的费用,假期里冒着危险去落后的个体煤窑当童工,每一次背着百十斤的煤,在黑黑的深深的巷道一阶一阶的往上爬,累得骨松肉痛。而且这窑主就是那穿红戴绿对他还颇有好感的女同学媛的父亲,心里能平衡吗?尽管作者有意强化明震的男子汉的顽强性格,但生活与现实的逻辑是不能不令人思索的。而且越是长大,思索得越深。我想这其中滋味会深深地留在明震的心里,特别在煤窑出现事故之后,那是窑主的黑心造成的,虽然明震免遭灾难,但面对工友的死亡,他的心怎能不受伤得流血!
再比如小说《蓝山》,小主子二夯看不上小侉子。“因为他是爹的雇工”。这是小说的眼,也是小说的涵意所在。
在二夯的眼里,小侉子是个损相:“穿一条也许是他妈、他姐的裤子,肥,大,还是偏门儿的,旧军衣差点垂到膝盖上,公袄襟就缀了大小七八块补丁。一张小脸干巴巴,眼睛还有点近视。”连叫什么名字也没给记住。而且还想方设法“调理”小侉子,故意赶车轧石头。把小侉子跌下去;故意用土坷垃打树冠,让土落在小侉子头上。小侉子总是默默的,一声不吭,用发呆的近视眼盯着二夯。虽然小侉子的顽强坚韧与吃苦耐劳和那热爱读书的精神感化了二夯,使他有了读书的积极性,决意去城里上学,但二夯在小侉子心里留下的是什么呢?他可以原谅和忘却二夯的个体言行,可是他能忘却这段生活,忘却这种生活里小小的年纪所受到的伤害与屈辱,以及心灵洒下的泪滴?!
陈玉彬的少年小说创作是属于“开放式”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把学校的大门打开,让少处放飞生活的天地间。或者说,他喜欢甚至偏爱于在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里,描绘当代少年的形象,让他们涉足人生,在环境恶劣困难挫折中获得人生的知识的人性的品质,很少把小主人公囚禁在课堂和师生之间。另外,陈玉彬很关注社会底层的那些遭受贫困和种种不幸的少年。他的好多短篇的主人公都是那种经历苦楚顽强生活的小“男子汉”。他对生活中的少年强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着力赞美那些已经不容怀疑的小“社会人”。
陈玉彬“开放式”的儿童文学观,给他的少年小说创作带来很大的益处。令他放开了手脚,使作品变得内容丰富、色彩斑斓、场景开阔,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读来也活泼生动,毫不沉闷,很生活化,不时还能领略某些地域的文化风情,这种感觉是与读那些编造的、教化的、概念的、无生活滋味的儿童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这是一种正经的文学享受。儿童文学文学化,是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