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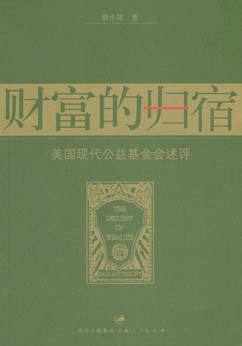 如初版前言中所说,本书原意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着眼在帮助国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如果有所启发,也是原则上的,比较遥远,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我认为国情相差太远。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于2003年问世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不少报刊登载了评论文章,本人也应邀接受了许多采访,并在不同场合就这个问题作演讲。特别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因此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过去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和以不同方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因为除了少量翻译著作外,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而当前正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和公益家茅于轼在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大意):20年前我国开始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大家对于“赚钱”之说极不习惯,因为完全违反了我们过去30年所受的教育;现在又是180度大转弯,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生财致富之道,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告诉大家怎样花钱以服务社会,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惊奇。回顾这20多年的改革,变化之大,进步之快,恐怕都是空前的。 如初版前言中所说,本书原意是作为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着眼在帮助国人从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如果有所启发,也是原则上的,比较遥远,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我认为国情相差太远。出乎意料的是,本书于2003年问世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不少报刊登载了评论文章,本人也应邀接受了许多采访,并在不同场合就这个问题作演讲。特别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因此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过去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和以不同方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因为除了少量翻译著作外,这是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综合介绍和分析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而当前正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和公益家茅于轼在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大意):20年前我国开始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大家对于“赚钱”之说极不习惯,因为完全违反了我们过去30年所受的教育;现在又是180度大转弯,全国上下都在讨论生财致富之道,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告诉大家怎样花钱以服务社会,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惊奇。回顾这20多年的改革,变化之大,进步之快,恐怕都是空前的。
在他们的评论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正经历着迅速的发展。其原因是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与本书的主旨有关:
(1) 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富翁,而另外的亿万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缺乏最低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公开讨论的热门话题。
(2) 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对社会公益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除了刚才提到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社会变化而涌现出来,例如: 由于人口老龄化、传统家庭解体以及“空巢”现象等因素同时出现而日益严重的家庭问题,流动人口的权益与福利问题,环保问题,毒品问题,卖淫问题,艾滋病与其他流行病问题等等。其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失学问题尤其显得尖锐突出而影响深远。单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社会公益力量的介入。
(3) 旧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显然,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都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和团体来解决。旧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全靠党和政府的体制早已失效,何况即使在那个时期实际上也没有全包,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口不在该体制内,更不用说农村。现在政府财政正在从各种以前的福利领域退出,更遑论如此大量的新的需求。因此,需要填补的真空相当大。再者,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和期待在不断提高,有了与国际的横向比较,也就更容易增长不满情绪。
(4) 私有部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稳步增长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实际上存在已久的事物终于在1999年修改的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2004年修正的宪法中又进一步承认了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应该说是带有划时代性质的。这一举措除了带来其他效应之外,更鼓励了私人对公益的捐赠,从而促进私人公益事业的发展。
(5) 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有所提高。尽管当前社会和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但就全社会而言,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需要除政府以外的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特别是公益事业进入了企业的关注范围,积极公益的企业家也日益增长。另外,志愿服务也开始提上一般人的日程。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热心的公益事业活动家和组织者。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根据多年这方面实际工作的经验,称本书为“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他读本书后提出六点与我国现实有关的体会,最后集中提出三点意见:
(1) 政府应加速制定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管理的法规和条例,创造一个有利于非营利组织以及基金会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2) 弘扬中国扶贫济困的传统理念,坚持“授人以渔”的方法,建设非营利组织步入自我管理、自我制约和专业化运营的发展轨道。
(3) 非营利组织必须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与他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我国这方面的形势有迅速的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不仅是媒体和学者的呼声,而且进一步为政府公开承认和面对。2005年“两会”政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以后,各级政府都纷纷对此有所关注,有所行动。
现在本书得以重版,令我欣慰。此书初版于2003年,资料截止于2002年。这几年美国当然又有许多新情况,作者不可能重新收集补充。不过本书主要是评述这样一种事物的起因、背景、作用、理念、规则,事例的多少不足以改变其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