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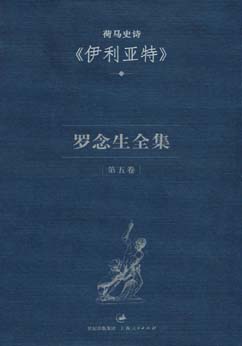 浪漫派的“病态”正体现在它的不妥协性上。伯林认为,它起源在德国不是偶然的。浪漫派在后期也寻求与现实的一定妥协。正是这一经验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对多极文化的认可、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伯林本人一生所推崇并为之奋斗的精神。 浪漫派的“病态”正体现在它的不妥协性上。伯林认为,它起源在德国不是偶然的。浪漫派在后期也寻求与现实的一定妥协。正是这一经验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对多极文化的认可、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伯林本人一生所推崇并为之奋斗的精神。
以赛亚·伯林爵士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不仅在学术界成就辉煌,也在政界积极活动,另外还是一位名正言顺的“公共知识分子”。德里达或哈贝马斯虽是这个名词的创始人,但和伯林相比,却相形见绌。他一生中频繁在BBC等大电台作讲座,其中,1966年在BBC电台关于浪漫派的系列讲座1989年最后一次重播,直到最近才被笔录,编辑成书。1997年逝世的伯林一直反对在他生前出版此讲座,原因是他计划撰写一部浪漫主义运动的专著,讲座形式过于松散,不适合成书。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现,不过讲座的编辑者哈迪认为,这不见得遗憾,讲座的书面稿保存了口头演讲的优点,伯林非常擅长口头表达,读来很是亲切。
说到浪漫派,我们总是首先想到的是雪莱、雨果,也许我们还会联想到激情、青春等名词,认为浪漫派主要是一个文学流派。事实上,这些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浪漫派也是一个政治运动、思想流派,它起源在德国,尽管其启蒙者、代表人的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哈曼作为浪漫派的最初倡导人也许只为专家所知,作为人类学的创导人赫尔德倒还为我们所熟悉,但有多少人真正读过他的论文呢?诺瓦利斯、提克、霍夫曼对读者来说,更不是响当当的名字了。这也许与德国文学的国际地位有关。
18、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文学相比,反映了一个局限的社会现实:当巴黎、伦敦成为现代工业兴起的大都市,德国小城镇的宁静还未被打破。生活的单调、社会发展的缓慢使得德国文学素材贫乏,难以与法国文学竞争。但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也适合深思,适合哲学、音乐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娱乐性是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经典作品如《包法利夫人》或《伊利亚特》等并不缺乏娱乐性。但德国浪漫派的文学作品却着重强调思想的表达、个人内心的表达,这给它们的普及制造了障碍。有趣的是,这也正是20、21世纪现代作品的特点。
出于同一原因,德国浪漫派中的哲学代表人物成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不灭明星。费希特、谢林、施勒格、马克思是哲学课的必修作家。德国浪漫派的主要特征是反对启蒙运动的教条,即相信有普遍、永恒的真理,相信每个问题都会有科学的解答,相信人类理智的力量。“狂飙突进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最早的反抗,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维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能以自杀作为反抗,但歌德很快认识到这种看法的局限性和极端性,不久就转而寻求别的出路。他曾说:“浪漫派是病态的。”他的成熟之作《亲和力》中也明确指出脱缰的激情会带来致命的恶果。
浪漫派的“病态”正体现在它的不妥协性上。伯林认为,它起源在德国不是偶然的。当时,德国在欧洲的文化上处于弱势,而法国文化是灿烂的启蒙文化,伏尔泰、卢梭、拉辛等是使我们今天仍产生敬畏之情的名字。德国对法国文化的反抗也就成为了对启蒙文化的反抗。同时深受路德宗教改革影响的德国新教徒怀有深沉的虔诚,反对把信念概念化、理性化。这造成了浪漫派注重个人的经验式表达、崇拜天才的现象。在政治上,浪漫派推崇行动,认为个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达到自我实现。但是这种行动是自发而无计划的,他们强调行动激情和献身精神,目标倒成了次要的。
于是,来自不同文化、持有不同信念的流派都能被称为“浪漫派”,只要他们在行动中具有同样的激情。但是他们的思想信念很可能互相冲突,那些信念在现实中的绝对实现也必然是不可能的。歌德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浪漫派的后期也寻求与现实的一定妥协。正是这一经验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对多极文化的认可、宽容精神。这也正是伯林本人一生所推崇并为之奋斗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