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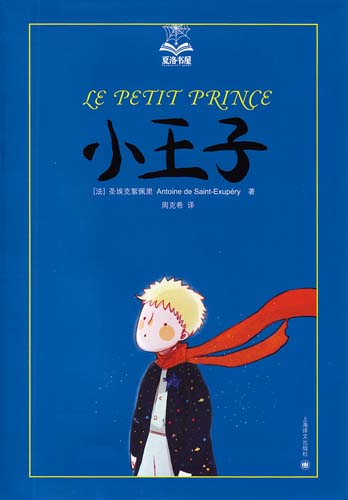 和周克希聊天,发现他是个儒雅、安静的人,但从他的译作中,你又很难读出他的性格:《侠盗亚森·罗平》中,他的文字活泼、灵动;《基督山伯爵》的译文注重时代色彩,浓墨重彩而又生动流畅;《追寻逝去的时光》,因为原文是法国语言文字的高峰,所以周克希翻译起来,追求清新典雅、举重若轻的风格,用他的话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周克希聊天,发现他是个儒雅、安静的人,但从他的译作中,你又很难读出他的性格:《侠盗亚森·罗平》中,他的文字活泼、灵动;《基督山伯爵》的译文注重时代色彩,浓墨重彩而又生动流畅;《追寻逝去的时光》,因为原文是法国语言文字的高峰,所以周克希翻译起来,追求清新典雅、举重若轻的风格,用他的话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去年5月,周克希将自己的翻译手稿及译文集签名本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今年下半年,上图将展出这些手稿,并将手稿编辑成书。近日,周克希接受本报专访,他说:“我有幸既遇到好家人,好老师,又结识好朋友,他们指点我、鼓励我、帮助我,使我在既有欢欣更有艰辛的文学翻译之路上一路走了过来,留下了一些浅浅的印痕。”
【周克希简介】
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代表译作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以及普鲁斯特系列长篇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二、五卷等。
1 “有些译稿,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对我个人而言,有某种纪念意义,比如,上面留有父母为我誊写译稿的手迹,或者记录着朋友对译稿的修改意见等”
周克希坦言,他一直对前辈的手迹很有兴趣。他的随笔集《译边草》虽然是写翻译的,但也加了几幅手迹插图:汪曾祺、普鲁斯特、奥斯丁的手稿,“手稿让我对作者有一份亲近之感。”周克希说,他曾看到汪曾祺在一篇小说后面用小字写的“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泪不能禁”,心里软软的。
有了电脑之后,手稿越来越少。但周克希还是给自己定下规矩:先把译文信手写在纸上,七涂八涂改上一两遍后再录入电脑,在电脑上改定。“这些涂涂改改的初稿,像我这样的普通译者,一般不会刻意保留。但有些译稿,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对我个人而言,有某种纪念意义,比如,上面留有父母为我誊写译稿的手迹,或者记录着朋友对译稿的修改意见等。”
在一次讲座上,我通过大屏幕上的PPT见过周克希的部分手稿,只见译稿边上满是颜色笔的勾画,有时一字之差,也要涂改两三个墨团。
上了年纪后,周克希开始考虑藏书、手稿的归宿问题,正巧上海图书馆来联系收藏手稿一事。“我很感激上图,给了它们这么好的归宿,只是被收入‘名人手稿馆’令我有些惶恐不安。”在捐赠《包法利夫人》《小王子》《基督山伯爵》《追寻逝去的时光》手稿的同时,周克希还将自己译文集的签名本一起赠送给了上图手稿馆。此外,他还选取了所翻译的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二十一个段落,用毛笔抄写,取名“追寻廿抄”。
下半年,上图将展出这些手稿、签名本和书法作品,并将手稿编辑成书,取名《译之痕》,以飨读者和翻译爱好者。
2 “在这几年里,我的父母相继去世,如今每当见到他们抱病为我誊写的一稿,我的心头就会变得异样沉重……”
用周克希自己的话说,“译之痕”是翻译生涯中留下的痕迹,是一种回顾。回顾他的大半生,他用“三十年数学,三十年翻译,中间交叠十年”来形容。
1959年,周克希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进入华东师大数学系当了老师。“文革”中,周克希偶然结识了上外法语系老师蓝鸿春。于是,他每周去蓝老师家一次,学习一小时法语。“我酷爱读小说,读中学时,几乎一天看一本书,学法语的初衷也只是为了能读点法文小说。”周克希回忆。但蓝鸿春很认真,让周克希不好意思不认真学。周克希向蓝老师学了将近两年法语,“她家在淡水路的小楼,在我心中留下温馨的回忆。”
1980年,华东师大公派周克希去了法国,两年里,他读到了更多的法语文学,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应该更宽广些。回国后,周克希仍在数学系任教,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1984年初,周克希在校图书馆看到都德的长篇小说《不朽者》,这让他动了翻译这本小说的心。他译得很投入,花了4年时间,年迈的父母也曾帮着誊抄译稿。但那几年,周克希度过了心里最难受的日子,他在《不朽者》的译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这几年里,我的父母相继去世,如今每当见到他们抱病为我誊写的一稿,我的心头就会变得异样沉重……”
在周克希的翻译道路上,有很多亦师亦友的前辈。三十多年前,当时,还只是翻译“票友”的周克希带着自己誊抄的译稿拜访了翻译界前辈郝运。“在我想象中,郝先生应该住在一栋面对草坪的小楼上,精致的大书橱里摆满外文书,喝着咖啡,说不定还抽着烟斗。”但到了那里,周克希发现,郝运住在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子里。还要穿过几家合用的厨房,爬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最终才在一堆凌乱堆放着的稿纸后面见到了偶像。令周克希欣喜的是,他的翻译习作得到了郝运的肯定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