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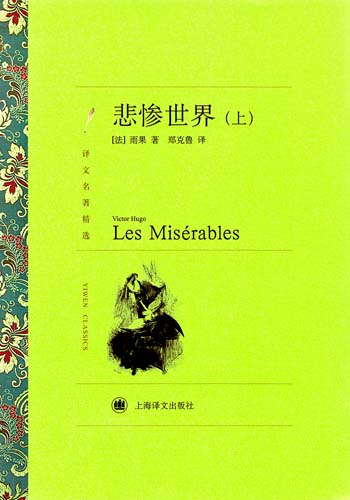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兼法语系主任。法语文学翻译家。 □袁筱一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兼法语系主任。法语文学翻译家。
可能没有一部小说像《悲惨世界》一样受到影视的青睐:从1907年,第一次电影改编,还是默片的《街垒上》开始,《悲惨世界》已经有了不下三十个电影版本。我们可以不动脑筋地推论:伟大作家终究是伟大作家,他不需要借助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来推销自己,而是其他更具感官效果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他的作品来言说。
因此,袁筱一用这样一种方式阅读雨果:通过《悲惨世界》去阅读雨果,在雨果虚构的故事里,体察这位伟大作家的悲悯、理想与爱。历史会终结,生命永不止息,而善与恶的博弈,也是永不止息,唯一的安慰或许是重温一遍雨果关于人性的简单梦想:择善固执。
浪漫:在某一时刻,我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
我对《悲惨世界》的印象,是不知道在多少年前,读的什么版本里,那个拿着巨大的扫帚(或者是拖把?),瞪着一双大眼睛的珂赛特。她是如此“悲惨”,在寄养人家被人呼来喝去,挨冻受饿,还因为经常挨打挨骂而瑟瑟缩缩。小女孩不漂亮,冉阿让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八岁的小女孩“体瘦面黄,她已快满八岁,但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六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光彩”。
珂赛特这个人物很是神奇,属于小说的神奇:前一秒钟,她还是可怜的灰姑娘;然而后一秒钟,冉阿让已然出现在她的生命中,这位看上去并不富有的老人竟然一掷千金,先是买了她连觊觎之心都不敢生的漂亮娃娃,接着又买了她的劳作时间,最后,当然就带着她走出了地狱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最要命的是,在某一个时刻,在卢森堡公园里,在年轻男子马吕斯眼前,曾经的灰姑娘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当人们走过她身边,她的全身衣着吐着青春的那种强烈香气。”——雅致、挺秀、脱俗,强烈香气,任何一个读者读了这样的词语,大概都会不自禁地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美丽的侧影,而这侧影,又让我们不自禁地要和封面插画里,眼睛里盛满了悲愁的小姑娘两相对比。我相信——第一次读到《悲惨世界》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在某一个时刻,我大约的确把《悲惨世界》当做童话故事来读的。也是在这个时刻,我理解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含义。
人性:虚构背后的正义梦想
雨果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悲惨世界》里固然包含着这个灰姑娘的故事——而且还有王子和公主的爱情——,但它更是冉阿让的,那个在小说一开始就偷了米里哀主教银器的苦役犯。是米里哀主教的宽容将冉阿让彻底从恶的一边拉了过来,进入善的世界。后来的冉阿让是市长先生,也是将珂赛特从悲苦中带入天堂的“圣父”。他不再愤懑地仇恨社会,而是一方面追着赶着承认自己是遭到缉捕的苦役犯的事实,另一方面却又为身边的每一个穷人——或者我们在狭义的范围内所理解的敌人(例如沙威)提供帮助。
雨果要写一部关于穷人的小说:有冉阿让、芳汀、小珂赛特,穷大学生马吕斯,还有已经做了主教的米里哀;当然穷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穷人中也有罪恶的德纳第夫妇,还有介乎于善与恶之间的爱潘妮等等……除了马吕斯的外祖父吉诺曼先生是唯一的资产阶级(而且没什么财产)之外,《悲惨世界》里都是穷人,是十九世纪巴黎和外省的底层或者接近底层的民众。相对于小说所容纳的历史厚度来说,《悲惨世界》里的人物并不复杂,但这不妨碍它能够从贫穷这件魔术师袍子中拿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在这些彼此呼应的故事里,有雨果要论述的正义、历史、爱情和在雨果看来最最重要的人性。
再次想到,并且重新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竟然又一次亲近了这幅尽管悲苦——那是西方社会在十九世纪工业、政治革命后多少都经历过的悲苦——,却不乏理想化的画卷。这个冉阿让从“恶”(一个苦役犯,一个小偷,一个连小孩子四十个苏都要抢的“恶人”)中猛然顿悟,从此一心向善的故事。或许每一个熟悉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读者应该都热爱过这样的传奇故事,相信这是小说才能够虚构出来的传奇。再次阅读,仍然会为在这种虚构背后所牵涉到的理想和激情唏嘘不已。
可不是吗,我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一切:没有显现为荒诞怪物的历史,充满理想与爱的人,有好的收场的善良的人们。
历史:永远终结不了的却是“人”
历史在雨果的笔下是有逻辑的,而在雨果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们看来,他们的责任正在于揭示这份逻辑,从而使得历史的逻辑更趋向于合理,更能够符合“人”的需要。在历史的这个问题上,雨果与巴尔扎克或是欧仁·苏所不同的只是,出于浪漫主义的偏好,雨果喜欢“大事件”。几乎所有雨果的小说里都有历史的大事件,那是除了爱情之外,能够给雨果带来激情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