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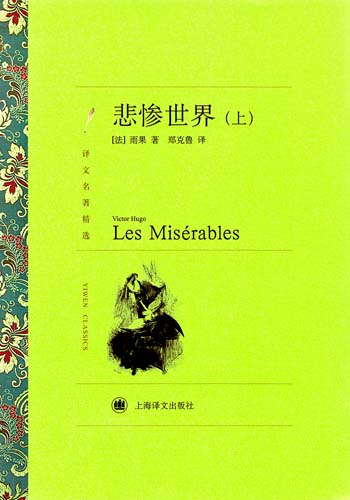 没有汤姆·霍珀执导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前些天的奥斯卡颁奖礼恐怕就要被李安专美了。毕竟在以明星,尤其是女明星为本的奥斯卡现场,当红的安妮·海瑟薇,在那届星味颓靡的典礼上,实在是杀伤力强大。放到中国内地也一样,不少观众看《悲惨世界》,一少半是奔着音乐剧,一多半是奔着安妮·海瑟薇和休·杰克曼去的。在他们眼里,“明星-音乐剧-雨果”才是正确的选项次序。当然在导演那里,这一次序应该是:音乐剧-明星-雨果。 没有汤姆·霍珀执导的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前些天的奥斯卡颁奖礼恐怕就要被李安专美了。毕竟在以明星,尤其是女明星为本的奥斯卡现场,当红的安妮·海瑟薇,在那届星味颓靡的典礼上,实在是杀伤力强大。放到中国内地也一样,不少观众看《悲惨世界》,一少半是奔着音乐剧,一多半是奔着安妮·海瑟薇和休·杰克曼去的。在他们眼里,“明星-音乐剧-雨果”才是正确的选项次序。当然在导演那里,这一次序应该是:音乐剧-明星-雨果。
“小清新”和文化人看电影时据说都哭过。这首先是导演汤姆·霍珀的功劳。把一部著名舞台剧搬上银幕,叙事空间、表现手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体技术环节上的问题,注定会层出不穷。演员的表演展示,也由舞台上的声音和形体,不可避免地要扩展到面部特写……像这样一部由音乐剧名著改编的电影,在立项之始、尚未确定导演之际,通常便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而舞台剧改电影肯定是要遭骂的——
首先,重场戏之间的常规过渡肯定压缩,熟悉的观众会不适应,觉得局促。这跟京剧《借东风》或是话剧《屈原》拍成电影后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其次,有观众挑剔演员嗓子不够好,又总给个大脑袋特写。嗓子不好就对了——因为都是卡拉OK水准的电影明星在唱。估计是考虑拍电影,舞台剧演员没电影演员在镜头前自如的缘故。而明星出演,如果不给大脑袋特写,怕是不会接拍的。艺术和钱景的因素都有。唯因如此,也才会构成些全球性谈资。
以《国王的演讲》导演身份,执导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汤姆·霍珀是冒了风险的。最后把片子拍到能赚人眼泪、能拿奥斯卡,还能进入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时尚话题,从世俗层面讲,是个不小的成功。
话说回来,因为“嗓子不好”,成功了的《悲惨世界》在“音乐剧电影”这个具体分支里地位还有些尴尬。一方面,它在影像方面做得非常时鲜;另一方面,它在演员的气质吻合和音乐质素方面都有一些错位。就年龄和外形而言,拉塞尔·克洛显然比休·杰克曼更适合演冉·阿让,其他演员,包括安妮·海瑟薇,大多数情况下,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在演发生在英国的故事,而不是法国的传奇(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英国另一位导演乔·怀特去年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编上)。作为音乐剧,演员对《悲惨世界》的唱段演绎,实在谈不上多么动听,有些地方还不如把唱词说出来舒服。这些遗憾,又很容易对电影产生“为票房而急就和拼凑”的感觉。
《悲惨世界》:作为成功的文学名著
在今天,无论是观众还是导演,大家在看待这部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时,雨果及其原作都是绕不过的。但无论如何,雨果肯定又都不是观众买票、投资商注资的第一选项。商业与文学一旦冲突,被牺牲的一方,显然是不会说话的原著,和已故作者。
看汤姆·霍珀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的观众,有不少据称哭了。好事,因为哭过,个别人可能还会去找雨果的小说原著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把名著当名著待见,也日益拒绝为名著精神继承人提供生长空间的年代,在这个背景下,任何能将大众注意力引向文明精华的时尚热闹,都具有了渡船的功能。不过,凡名著被改编,又都会面临被后世人做减法的尴尬。怎样在重读名著以及读解“名著被改编”这一行为的过程中,把后人自作聪明删减掉的珍宝恢复原貌,这是我们重新直面原作时必须认真去做的。
在几乎所有的英美舞台和影视改编版本中,《悲惨世界》不过是冉·阿让逃亡、抚养孤女的故事。芳汀、沙威和珂赛特以及其他人等,均是为了构成、铺排这个故事而展开。其实呢,如果不是为了阐述自己的世界观,雨果不一定非要花那么大笔墨去演绎冉·阿让的行迹的。大作家的价值不是去讲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在于通过精彩的故事,去更精彩地呈现生活的滋味,并在这些五味俱全中揭示不同类型的人,他们作为“人”的困惑,他们彼此的冲突与宿命。
小说不需要表现寓意和训诫,即使是作为“人道主义名著”的《悲惨世界》,它所表现的也不是个人如何融入大时代、融入上帝之光,而是:一个认真活着的人,怎么使用好他自己的生命,怎样把他遭受过的不幸,尽量在他人的生命中抹去。谁都不是救世主,谁都可以发出自身有限的“圣人”之光。每个罪犯的身上都有一个冉·阿让;每个正直的、有原则的人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个沙威;德纳蒂的贪念,它是我们每天都能遇见的——在他人和自己身上,有时还是同时……而所有这些,维克多·雨果并没有像导演汤姆·霍珀那样自信地指着大家的鼻子,对我们进行灌输。雨果只是讲了一个人的改变,他改变后的承担,以及这承担的艰辛、凶险和微不足道。好的文学家,从来都是强调一下后者的,而宣传家们,却习惯于把微不足道升格为“主义”——即便是市场和资本家的宣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