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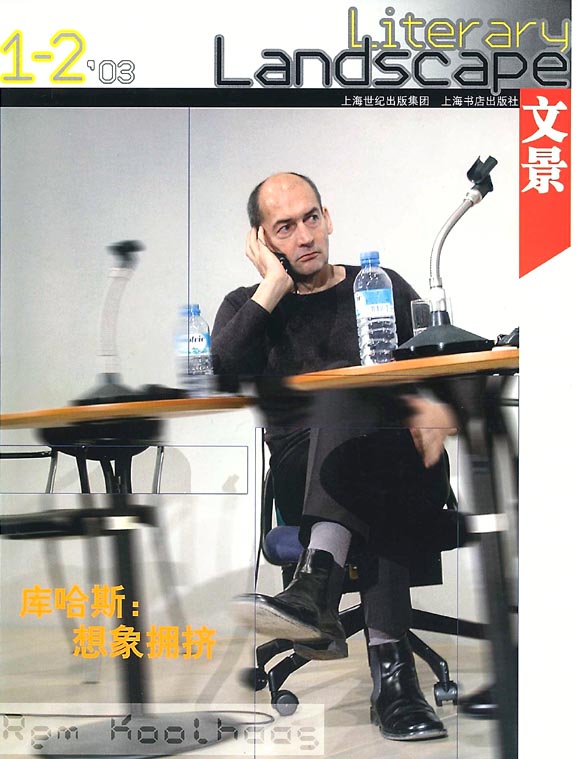 如今,提起一两年前的事,一个时髦的说法是:“上个世纪末”。这平平淡淡的几个字极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的人生仿佛一下子被拉长了,素来隔膜的历史烟云正太阳一般悬挂在我们日常的头顶。我们被“新千年”、“跨世纪”之类的媒体语汇突然冲击,一种人类发明的数字巫术正蛊惑着我们的心智。就像央视春节联欢会的“撞钟”仪式引起的欢呼一样,“世纪之交”的人为盛典也流感一样潜入地球村的每一扇窗户,于是,黄口小儿的几声咳嗽听上去也陡增了许多“历史感”。 如今,提起一两年前的事,一个时髦的说法是:“上个世纪末”。这平平淡淡的几个字极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的人生仿佛一下子被拉长了,素来隔膜的历史烟云正太阳一般悬挂在我们日常的头顶。我们被“新千年”、“跨世纪”之类的媒体语汇突然冲击,一种人类发明的数字巫术正蛊惑着我们的心智。就像央视春节联欢会的“撞钟”仪式引起的欢呼一样,“世纪之交”的人为盛典也流感一样潜入地球村的每一扇窗户,于是,黄口小儿的几声咳嗽听上去也陡增了许多“历史感”。
如果我们的记忆力足够好的话,两三年前发生的事应该依稀记得。那时,文化界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到处都在“盘点”,且算的都是“世纪账”,“百年账”。很多人被时间的灰尘呛得咳嗽,流泪,有的干脆患上心肌炎。在学术圈,“综述”类文章最为抢手,怀旧的气息弥漫;而文坛,不知怎么竟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盘点”升级为“清算”:这里在上演名为“断裂”的行为艺术,那里在宣读致20世纪文学的“悼词”;北京有人在“剥”大师的“皮”,陕西有人在搞“十作家批判”;鲁迅也好,金庸也罢,见一个“灭”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周星驰理当“优待”……这种“狂欢节”般的言说盛况正应了一千多年前,钟嵘在《诗品序》里所作的描述,真是“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诚然,这些经过精心策划的“世纪末言说”大抵都有较强的观赏性,然而观看了太多的“文化杂耍”之后,受众的味蕾开始麻痹,面对文坛小子们的“生猛表演”,我们总算学会了报以几声哈欠。我的渐渐趋于鲜明的态度是:如果那些炙手可热的出版物老是贩卖奇谈怪论和别字病句--就像不学好的盗版书--不去凑那个热闹也罢。这么说,是否偌大一个图书市场真就找不出几本“养眼”一点儿的书呢?那倒也不是。手边这本书就让人感到欣慰。这就是骆玉明先生的新著《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读这本五百多页的书,你会觉得作者很下力气地在发掘着什么,他的目光在流年岁影中穿梭游移,在白纸黑字中绕来绕去,不紧不慢的叙说,棉里藏针的点逗,黍离之哀,人琴之悲,就那样一笔一笔地皴开去,一波一波地漾开来,遂让人唏嘘咏叹,不能自已。但也不必担心嗅觉里会一直弥漫着历史的霉味儿--再怎么着这也是伸手可及的“近二十年”,更何况作者取景框里的人,有几位好好的还在。“人们关注名人终究是为了关注自己,是为了从中得到对所处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在世间生活的资财”。这是作者在《引言》里的一句话。我承认我对这话的理解透着俗气,因为它让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对照一下作者选取的对象--李泽厚,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我还真就不觉得唐突。试问这些人物当中,哪个不是为不同趣味的人曾经爱着、正在爱着或还将爱着的呢?面对这些先后对20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化生态”产生过不同影响的人物发言,对谁都不是一件便当的事,一不小心触发了什么引线,招来些不必要的是非,原也极正常。而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却相当之好,在一个不小的圈子里,几乎是“奔走相告”;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人们校正自己对这些“热点人物”观感和认识的一个潜在坐标。如果作者没有“爱”--对笔下人物也对自己--取得这样的成绩就不仅不易,而且几不可能。
正如书的封面赫然标明的,《述评》属于“编著”之书。书里的一部分内容,是海内外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的精心选班,另一部分是作者所写对上述名人的述评文字,以及对所选文章的“说明”;后者在表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有提要意味和连缀作用。作者说,“这一种结构似乎有些怪特,但考虑到既要保存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颇为珍贵的资料的原貌,又要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遂处理成为现在的样子”(骆玉明:《说起那些名字》,《中华读书报》2001年2 月28日)。该书的体例一如上述,而其目的也如作者所说,乃在于“多少引发一些思想”,给爱读书的人“提供一种有意义的阅读”。作者恐怕没有想到,这一部“结构似乎有些怪特”的书所引起的阅读反应也颇不一般--编选的文章固然增加了书的厚重,但是,“骆玉明怎么说的”更成了读者视线的焦点。因为是“编著”,选出的文章原本散见于各类读物,其各自的独立性已经确立,故而这书的“活页”效果就很突出,骆氏的9篇“述评”和为数不少的“编选说明”(计52篇)不仅完成了“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的任务,而且,其自身亦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系统。据我所知,将作者的述评文字率先拈出一睹为快的人不在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