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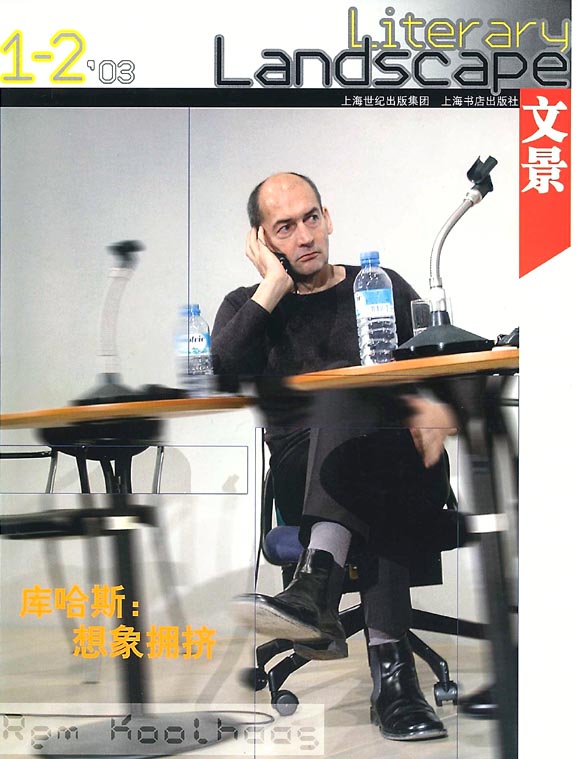 如今年代,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喜欢通过阅读童话、漫画、卡通来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某档爱情速配节目中,女嘉宾送给男嘉宾的礼物是本精心挑选的漫画书;办公室里,两位同事模仿着蜡笔小新的语调互相调侃,“你不答应,我就告诉不认识的叔叔你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书店里,为朱德庸、几米的漫画掏腰包的不少是成年人。有人把这股时尚潮流称之为“成人儿童主义”,还有的干脆宣布,成人找到了安慰的“奶嘴”。 如今年代,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喜欢通过阅读童话、漫画、卡通来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某档爱情速配节目中,女嘉宾送给男嘉宾的礼物是本精心挑选的漫画书;办公室里,两位同事模仿着蜡笔小新的语调互相调侃,“你不答应,我就告诉不认识的叔叔你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书店里,为朱德庸、几米的漫画掏腰包的不少是成年人。有人把这股时尚潮流称之为“成人儿童主义”,还有的干脆宣布,成人找到了安慰的“奶嘴”。
儿童主义也好,奶嘴也罢,这样总结式的命名暴露出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童话、漫画和卡通原本是儿童的专利。的确,在物质条件匮乏、文化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人们的文化消费非常单调和雷同,很多人除了阅读文学作品别无选择。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图书、影视、音像、互联网等多种样式相继出现,读者选择面更加宽泛和多元化,出现阅读的分流是必然的趋势。
显然,用“儿童主义”不能完全描述上述现象。商业化运作和产业化经营使文化市场越来越趋向于细分。比如,在漫画发达国家日本,漫画实行分级,有给孩子看的漫画,也有专门面向成人的,其中,成人漫画的市场还相当广阔。漫画的勃兴也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影视、玩具、文具、纪念品等等,产业化规模相当可观。中国的成人漫画尚在模仿和起步阶段,但方兴未艾。
其实,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漫画就颇受欢迎。不仅诞生了众多的漫画专刊,《良友》、《时代》等大型综合性画报也都辟出专版刊登漫画。张光宇、叶浅予、胡考、郭建英等著名漫画家就是在那时获得声誉的。当时,叶浅予的长篇四格漫画《王先生》系列家喻户晓,其电影版也获得成功,这或许是漫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最早尝试呢。《王先生》讽喻时世、描摹世相,其阅读对象正是成年人。
这股被误称为“成人儿童主义”的潮流至少包括了几种倾向:一种是专门为成人度身定制的讽喻性作品,如与“王先生”殊途同归的讽刺性漫画《涩女郎》系列、日本卡通连续剧《蜡笔小新》等。前者以都市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为主题,再现了庸常、世故、贫乏的成人世界。轻浅的讽刺、善意的劝讽、简单幽默的构图和旁白,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很多人在一笑之余,似乎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影子。后者虽然讲述的是一个“道德”上颇有污点的顽童小新的故事,但暴露的却是成年男性的心理弱点:自私、好色、无赖、狡狯。这些缺点借助孩童的身份,取得了大家善意的谅解。
另一种作品以返朴归真为主题--或找寻真挚的情感,或反省成人世界的世故,追念失落的童真。如,几米的漫画、童话《小王子》以及安房直子的《蓝色的花》等。几米的漫画构图精美,他让图像“成为清新舒洁的文学语言”,“配上新诗一样的文字,描绘出都市人的感慨、幻想与梦”。他的画成为紧张都市生活中的润滑剂,带给年轻人温馨的情感慰藉,虽然失之肤浅和矫情。
《小王子》的好评实在太多,最耸人听闻的广告语甚至称它为“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的读物”。在此,我无意怀疑人们对这本书的真实情感,我想说的是,不要把它当作童话,把它当作寓言吧,因为它算不上一部好的童话。试问,有几个孩子愿意读并读懂《小王子》,除非他过早地告别了童年,领略了成人世界的人情世故。书中不乏蕴涵哲理的警句,但缺少奇思妙想的童趣逻辑。诚如作者所言,这是成人写给成人看的书,透露着拒绝长大的童心情结。
还有一种倾向,是从纯粹的儿童读物里,重温童年的快乐和梦想,或从老少咸宜的童话中,寻找属于成人的人生喟叹。比如,根据宫崎骏的童话《千与千寻》改编的同名电影,虽然没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但精灵古怪的幻想辅之以唯美的画面,给人以极大的视觉愉悦,受到很多成年人的喜爱。
真正优秀的儿童读物包括影视作品,总能赢得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夏洛的网》和《彼得·潘》就是这样的作品。青年学者严锋,以《夏洛的网》为“暗号”,结识了挚友包亚明,由于他的介绍和“义工”肖毛的热心翻译,《夏洛的网》在网上广为流传,一只拥有非凡智慧的蜘蛛和一头幸运的小猪之间的友谊,就这样感动了无数的成年人。同情、关爱和友谊蕴涵在妙趣横生的故事里,使人们读到了比故事本身更多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