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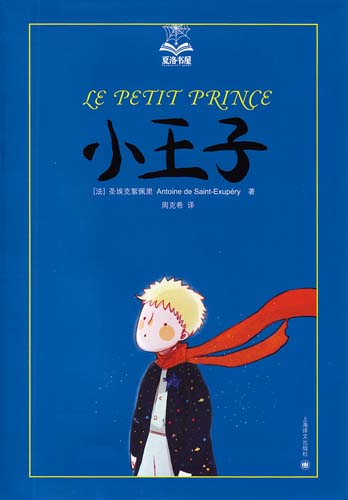 其实,有关文学翻译质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从村上春树的林少华和赖明珠译本之争,到对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质疑,甚至曾被视为“定本”的王道乾《情人》译本,也难逃被“挑刺”。 其实,有关文学翻译质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从村上春树的林少华和赖明珠译本之争,到对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质疑,甚至曾被视为“定本”的王道乾《情人》译本,也难逃被“挑刺”。
“日磨千字”铸就经典
如果对译作版本不挑剔的话,读者会在某本《堂吉诃德》的开篇里,读到这样的堂吉诃德:在村民眼中,他可是一位真正的贵族绅士。他家里收藏着一支又旧又钝的长矛,还有一面锈迹斑斑的盾牌,院子里,有一只灵敏的猎犬跳来蹿去,还养了一匹瘦骨嶙峋的马。
不过,在杨绛的译本里,这段话是这样的:他那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
两相对比,高下立现。诚如作家阿城有言,“翻译体可以接受,但翻译腔不可接受”。
学界对经典译者时代划分为:一是成长于“五四”前后的一批译著大家,如冯至、李健吾等;二是抗战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批译者,尤以西南联大的“九叶派”闻名;三是“文革”前毕业的一批专攻外国文学的大学生。
这三批译者,受后人尊重的程度,与他们的“日磨千字”的艰苦付出成正比。老一辈翻译家们,是在用生命成就名著。
以杨绛为例:杨先生在翻译《堂吉诃德》前,已经有多个版本的《堂吉诃德》由英译本转译至中文。为了忠实原著,杨绛不仅学习西班牙文,而且对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只把长句拆为短句,再把短句重作安排;如有疑义,还要参阅英、法、德、西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直至自信无误为止。这一磨,用了22年。
而当今出版界,大部分译者文学水平不及老一辈文学家,已是公认事实。对于名著的翻译侵权和剽窃,更是“蔚然成风”。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欧阳韬介绍,近年来,出版市场放开,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优秀译本的剽窃行为愈演愈烈。仅以该出版社《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一书成为抄袭对象为例:一些不法书商雇用写手,在已有译本上改动个别字句,调整一下句式结构,很快就能炮制出动辄数十本的外国文学名著“新译本”,以低廉的价格大行其道。不明真相的读者常常被这些装帧堂皇的“中译中译本”欺骗。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部主任黄昱宁有着二十余年的翻译经历。她对此只用一句话作评:“没办法,公版书是可以反复重译的,自然良莠不齐”。
根据相关出版法规,一般作品的版权保护期为作者死后50年。也就是说,在作者辞世50年后,经典作品再译可不用付版权费。而大多数经典外国文学名著,例如《堂吉诃德》《复活》《红与黑》等等,都超过了这一期限,可以免费随意出版,也就是“公版书”。
这样一来,重译和借鉴经典作品,就成了省时省力且稳赚不赔的讨巧活。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一批文学名著被各家出版社反复重译、再版,其中,《小王子》一书,据不完全统计约有60个中译本,这还不包括同一译者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本以及各类“缩写本”。
实际上,好一点的借鉴,是照着外文翻译,并与以前的译作进行比对;而更恶劣的借鉴,则是将前人译作里的中文,换一种说法写出来。
如此,读者就能看到内容大致相同,但文风完全不能匹配的名著了——这样的手法,不会落人口实,被指责为抄袭。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
除却抄袭和借鉴,那些真正埋下头来认真翻译版权书的译者,也正面临收入低微、狂赶“工期”,但仍因翻译质量被贬损为“无业界良心”的窘境。
以年初著名出版人路金波推出的李继宏版重译名著计划为例,该计划号称“一套涵盖19位西方经典作家的名著新译本”,“日译一万字”,不过,读者并不买账,这一计划尚未执行到一半,就被豆瓣网网友抵制。
另外,与公版书不断再译再出版相比,外国新一代文学大家进入中国的脚步,要么来得慢得多,要么忽然集中式爆发,但质量参差不齐。
以雷蒙德·卡佛为例,这位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极简主义”的短篇小说大师,其最为著名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早在1981年4月就已在全球发行,并红遍欧美读书界。但直到 2009年年初,肖铁翻译的卡佛短篇小说集《大教堂》面世,当年年底汤伟(小二)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出版,卡佛才终于尝到在中国走红的滋味。
另外,新晋诺奖桂冠作家如多丽丝·莱辛、赫塔·米勒等,近年来作品大规模集中出版,也均属此情况。
黄昱宁直言,稿费制度和版权书(新书)翻译限时出版制度,均是令新书无法顺利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一个诱因。
比如,一本公版书,可以没有任何限制,随时加印,随时翻译;而一本新进的版权书,从出版社交给译者的那一刻起,必须在18个月内翻译出来。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提速,而文字是个慢功夫,一旦提速,质量必然下降。
再来看看稿酬制度。现在的翻译稿酬大抵为,每1000字70元,而要保证质量的话,每天的翻译量不会超过2000字,也就是说,翻译如果仅凭翻译新文学作品为生的话,月收入最多只能达到4000余元。这实在不是一份高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