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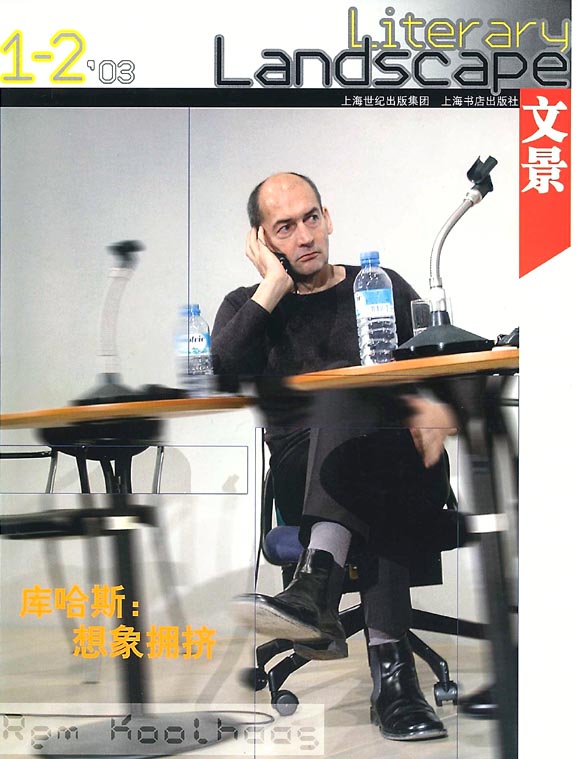 喜欢钻进故纸堆从遥远的过去里寻觅乐趣和慰藉的人,大概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会在一本纸张发黄变脆的书里,邂逅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家,他或她的作品也许算不上第一流的杰作,却有着别样的魅力。这些从岁月的幽深处漂浮而来的作品,哪怕只是一首小诗或是短短的一节文字,也会散发出诚挚、高贵的灵魂气息,让你不禁为之感动不已。 喜欢钻进故纸堆从遥远的过去里寻觅乐趣和慰藉的人,大概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会在一本纸张发黄变脆的书里,邂逅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家,他或她的作品也许算不上第一流的杰作,却有着别样的魅力。这些从岁月的幽深处漂浮而来的作品,哪怕只是一首小诗或是短短的一节文字,也会散发出诚挚、高贵的灵魂气息,让你不禁为之感动不已。
这样美丽的邂逅是永生的。我至今还能亲切地感受到第一次读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时内心强烈的震颤。那是在一个寒冷而清寂的冬夜,细密如网的雪霰挟着风撞在窗玻璃上,嘁嘁喳喳,宛如夜半私语。这样的夜晚最是惹人轻愁。我拿起一册英诗选熬,随手一翻,跳进眼帘的是克里斯蒂娜的那首《死后》:
帐幔半掩,洒扫一清的地上
铺着灯芯草蒲席,迷迭香和山楂花
缀满了我的床榻,
那儿,常春藤的影子穿过栅篱,慢慢爬移。
他俯下身来看我,以为我已长眠不起
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我却听见他说,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当他转过身去
降临的是一片沉默,但我知道他在流泪。
他没碰我的尸衣,也没有掀起
遮住我面庞的摺层,没有握住我的手,
也没有弄皱我枕着的光洁的枕头
我活着时他不爱我;可当我死了
他又怜惜我;这有多甜蜜
知道他温情尚存,尽管我早已僵冷。
这么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克里斯蒂娜竟诉说得如此平静,如此地优雅美丽。这里面没有丝毫的哀伤和怨恨,只有爱的温煦和欣悦。正如瓦尔特·罗利所说,这样贞静的歌声让你只想哭泣。这是感激的泪水,它带来的不是悲悼和感伤,而是一种明澈的了悟:在远离天堂的尘世,一切委屈、失意、哀伤和痛苦都是命运的馈赐,只有历经重重磨难,你才能照见天堂的光辉。
这就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她拥有一种惊人的才能,能把爱、悔恨、恐惧和虔诚这些令人悸动难平的激情,提炼成一种纯净平和的情愫,融入轻婉柔美的韵律和节奏之中。她的诗没有欢快明艳的色调,而是泛出轻浅的蛋青色泽,洁净透明,看似苍白稀薄,然而却是无比地柔韧坚实。对诗的形式和声音,克里斯蒂娜感觉极其敏锐,她的诗多半是凭着直觉写下的,结构匀称工巧,却又宛转自如,富于变化曲折。她对诗的节奏和韵律的把握和处理,尤其令人叹赏,每一首诗的音韵都异常和谐畅美,宛如天籁,让人想起风的叹息、鸟的吟唱,以及溪泉的幽咽琮琮之声。
克里斯蒂娜优雅圣洁的歌声,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为之倾倒不已。斯温朋在读到她的诗时,惊呼“再没有比这更辉煌的诗作了”,赞叹她的诗里回响着“天堂的明澈而嘹亮的潮声”;伍尔芙称赞“她的歌唱得好像知更鸟,有时又像夜莺”,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她列在英国女诗人的首位;福特·麦多克斯对她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她“是十九世纪贡献给我们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至少是英语语言的大师”。
克里斯蒂娜却是个顶顶腼腆的人,对这一片赞颂之声,她大概会稍稍感到些不安,也许还会羞红了脸。但她却完全无愧于这样的赞美。她天生就是个出色的诗人。在著名的罗塞蒂兄妹中,她虽然不像长兄D.G.罗塞蒂那般出名,但在诗歌的天分上却毫不逊色。虽然她的诗基本上局限于个人的情感和宗教体验,在题材范围上也许狭窄了些,但恰恰是这种自觉的限制使她的诗显得无比地纯净,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境地。
大概是感知方式和常人不太一样吧,在文学上有创造天才的人多半有点古怪。克里斯蒂娜似乎也不例外。童年时的克里斯蒂娜长得非常可爱,鸭蛋形的脸庞,漂亮的浅棕色头发,像榛果一样呈红褐色的明澈的眼睛,但脾气却刁钻古怪,是个叫人头疼的孩子。她很容易激动,情绪反复无常,动辄就要大发脾气,以至在家人眼里,发脾气成了她的正当权利,要是哪天她突然变得温驯友善,那简直要叫人惊奇得把这看成是她的慷慨馈赠了。幸运的是,罗塞蒂家庭中浓厚的人文气氛,使她潜在的文学创造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发展。她的父亲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是个流亡英伦的意大利诗人,对但丁的诗歌有着非常精深的研究。他常常给孩子们朗诵但丁以及其他意大利诗人的作品,罗塞蒂兄妹那样喜爱但丁以及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但丁的深刻影响,无疑和早年的这种熏陶分不开。老加布里埃尔还是个出色的歌手,嗓音浑厚迷人,每当冬夜降临,他便在熊熊的炉火前哼唱意大利歌曲或是古老的英国民谣,这些歌曲的优美旋律和朴挚的文词对罗塞蒂兄妹形成对诗歌音乐性的敏锐直觉肯定大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