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利弗写的并不是现代都市的晦暗幽秘的瞬间经验,而是我们人与自然相遇时,那种喜悦的、不可捕捉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她的诗之所以动人的非常核心的部分。奥利弗笔下的自然最终往往是非实体性,甚至是不可能的,正如在《这个早晨我看见鹿》这首诗中,她让一群鹿最终“进入不可能存在的树林”。
奥利弗的自然经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她一首诗叫做《中国古代诗人》:
无论去往何处,世界跟随着我。
它带给我忙碌。它不相信
我不需要。现在我理解了
中国古代诗人为何要遁入山间,
走得那么远,那么高,一直走进苍白的云雾。
从这里难以看到她对道家、佛教的核心精神的深入理解。对自然之象或相的观想活动没有在她的诗里展开,也未形成一种积极的内外双重运动,即,在观看外在世界之象的同时,在内在世界通过“心眼”的“造像”进行内在的想象和观看。
她笔下的自然与社会相对立,是为了抵消社会生活的时间强度和行动密度。她的自然观念是在对现代性的敌意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东方宗教让她获得了看待自然的方式,比如她在《蟾蜍》最后两节写道:
我谈论着世界在我看来是什么样的,五英尺高,蓝色的天环绕着我头顶。我说,蟾蜍就在那里,与尘土亲密无间,我想知道世界在它眼里是什么样的。
纹丝不动,不眨眼,也不皱眉,也没有一滴泪从那双金边眼睛里落下,当语言中提炼出的痛苦掠过它心头。(胡桑译)
诗集《我为何早早醒来》(Why I Wake Early,中文版名为《去爱那可爱的事物》)出版于2004年。开篇诗作《我为何早早醒来》可以代表整部诗集的核心追求。诗歌起始于问候——你好。紧接着,通过“脸上的阳光”,传达出对时刻、瞬间的接纳和领悟,对事物的开启和创造的思考:
你好,我脸上的阳光。
你好,早晨的创造者,
你将它铺展在田野,
铺展在郁金香
和低垂的牵牛花的脸庞,
铺展在
悲哀和想入非非的窗口——
在诗的结尾又出现了两个词——幸福和感恩。“瞧,此刻,我将开始新的一天,/满怀幸福和感恩。”时间的开启和创造最终指向完满的幸福,而幸福无疑源于对造物主的感恩。
奥利弗诗歌中一直有着对超验世界的敬畏。“光”对奥利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物。她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就叫做《光之屋》。整个屋子充满了光,也就充满了幸福,一种超验的幸福。《我为何早早醒来》第二节里追寻了“光”的超验来源:
可爱的星,正是你
在宇宙中的存在,
使我们远离永恒的黑暗,
用温暖的抚触安慰我们,
用光之手拥抱我们——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结尾一行具有强烈的仪式感,仿佛诗人和自然事物之间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瞥,而是犹如上帝在创世时投下的凝视。诗人接连说出三个词——“早上好”,这是朴素的日常语言,但已经脱离了日常语义,进入面对自然时的敬畏的瞬间。
于是,在这个仪式之后,一天才真正开始。也许我们并没有真正去开启每一天。时间的开启是精神世界的打开和醒来。我们需要在每一天清晨真正醒来,让那觉醒的风吹拂明亮的日子。让时间展开,让日子栖居在我们的生命里。正如弗罗斯特在《林间空地》中写的:
哦,寂寂温和的十月清晨,
让今天的时光慢慢展开。
让今天对我们显得不那么短暂。
(杨铁军 译)
《始于一次分神》
《始于一次分神》是胡桑的书评集,共收入从2010年至2018年间创作的书评,指向文学构筑潜能生活的能力。该书涉及辛波斯卡、米兰?昆德拉、略萨、马内阿、特雷弗、君特?格拉斯、鲁西迪、里尔克、帕慕克、阿兰达蒂?洛伊等著名的中外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胡桑秉承了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的细读方法,深入文本肌理,揭示文本写作的秘密,为读者开辟出诸多通往文学作品的条条幽径。通过胡桑的解读,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目击一个充满差异和竞争、最终能够和解的完整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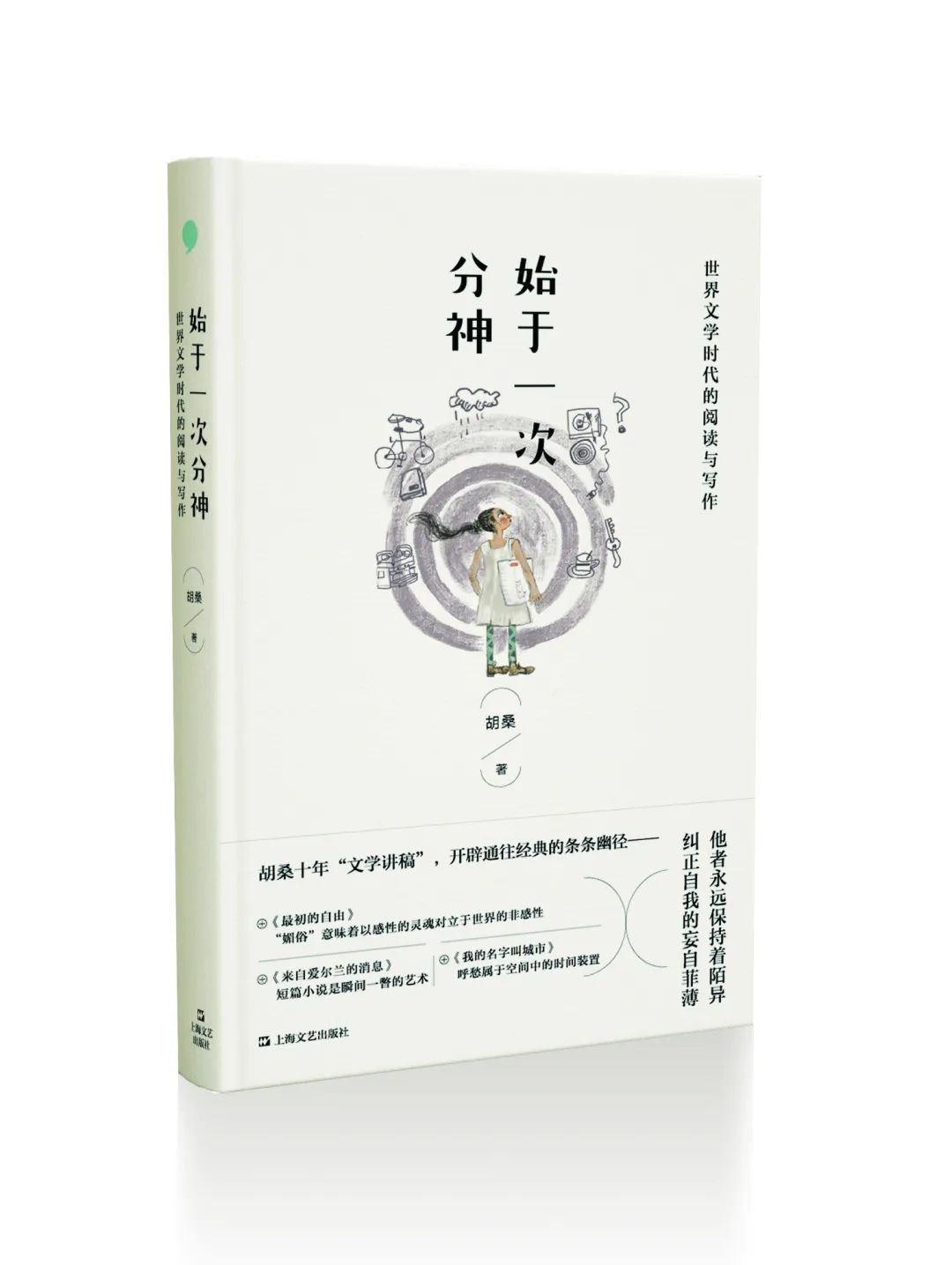
《始于一次分神》
胡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