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名对此两句诗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他认为这首诗用的是倒装法,写的是妆成之后的顾盼流波。“小山”指的是妇女头上的钗头,而“金明灭”则是妇女头上的金钗、银钗一类的头饰的光影和色彩。因她正在“照花前后镜”,所以发髻和金钗在镜中呈现随着自己的位置和光线的明暗不同而明灭不定,而下一句则承接前句,将云和雪这样的自然之物接续前句的“小山”,极力描写一个新妆的脸,粉白黛绿,金钗明灭。
废名的着眼点其实还不在于对“小山”一词的解释,而在于小山、金(山中灯火或星辰)、云彩或雪这样的自然之物,其实本与妇女的妆扮无关,作者却硬将这些本来子虚乌有之物与妇女的妆容加以并置,从而强迫读者对小山、金、云、雪展开想象,从而借用自然之物,来丰富对于妇女形貌的描绘。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废名的解读可能是一种误读,然而由于作者的词句中并未作出严格的规定,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忽略废名解读的有效性。退一步说,即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解读是错误的,这种有效性依然存在。顺便说一句,注释之于诗词欣赏,既是帮助,同时也是囚笼。
废名对另一位诗人李商隐诗的解读,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废名在修辞学上的重要发现。他在分析“姮娥无粉黛”废名的引文为“嫦娥无粉黛”,或是异文,不知所据。一句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作者“情理之无”与读者“想象之有”之间的复杂关系。
李商隐若正面写月色之皎洁,当然是“以有写有”,而此句的“无粉黛”,从“皎洁”的意义上来说,固是实写。但奇妙的是,李商隐却将与月亮决无干涉甚至抵触的“粉黛”意象拉入到诗中。通过“无”的否定,既保留了语言与所表现之物的逻辑联系,且未违反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
但“粉黛”这一意象一旦出现,就不是能够被“无”这个字所能轻轻擦去的——在指事状物的意义上,“粉黛”是一个“无”,它的确是被擦除了,但从联想的意义上说,“粉黛”始终存在,而迫使读者将月亮与粉黛一同想象,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文字上最微妙的“无中生有”。
这里有两个层次可以加以分析:在无的层次上说,它保留了语言指事的情理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的统一,可正因为“无”的存在,从中生出来的那个“有”,则具有无限的意象处理上的自由度。
“无”在实指意义上展开,而暗含的“有”则在想象、联想、类比等种种修辞意义上呈现意象的飞翔。正如“海不扬波”,“纤尘不染”,“也无风雨也无晴”一类的句子所带来的想象一样,读者不可能绕开“波浪”、“纤尘”和“风雨”等意象去捕捉它的实指意义。简单地说,逻辑上的“无”,恰好为联想中的“有”开启了想象之路。
李义山在《杜工部蜀中离席》中有“雪岭未归天外使”一句,常使人称赏不已。雪岭高耸、闭塞阻隔之意象,与“天外使”的意象并置后,天远云邈、山高水阔之境也同时出现于读者的想象中。“未归”一词则明确地告诉我们,“天外使”并不存在,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同样,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虽是用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语言文字最为重视基本的“象”,也重视经过逻辑推理后的那个抽象的“数”。通过“象”与“数”的结合,以类万物之情。但总体而言,对“象”的重视最为根本。这从《春秋》中占卜时对“象”、“数”的重视程度不同,就可见一斑。
但意象的有限性,特别是意象在状物时的种种逻辑限制,会对语言的表现力构成一定的影响,况且意象一旦使用,往往会因磨损而丧失弹性。这就迫使作者在寻找新意象的同时,通过设喻、取譬、类比或联想等技术手段,对“象”的功能、内涵、表现力进行进一步开掘,通过“有与无”、“象与意”,“虚与实”、“实有与假定”等复杂的修辞手段,化腐朽为神奇,来保持意象的活力,层层转进,愈变愈奇。
中国传统文学一方面十分看重语言的准确性,看重语言在指事状物方面的精当和贴切,另一方面对语言能否“尽意”更为关注。虚拟、象征、写意和联想所带来的自由、灵动甚至是暧昧,从“状物”的层面上来看,或许是对“准确”的一种反动,但从“尽意”的角度而言,恰恰是更高境界上的“准确”。
这就导致了“准确”与“模糊”之间的复杂错综。更何况,中国人所谓的“尽意”,诚如荀粲所言,是“尽而未尽”。正因为“言不尽意”,故而才需要“立象而尽意”;正因为意之幽微,非象所能包举,导致了“立象”修辞的复杂变化。
《文学的邀约》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论及一般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经验与想象、作者及其意图、时间与空间、语言与修辞。作者在细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的传统资源,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和辨析。同时,本书还希望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思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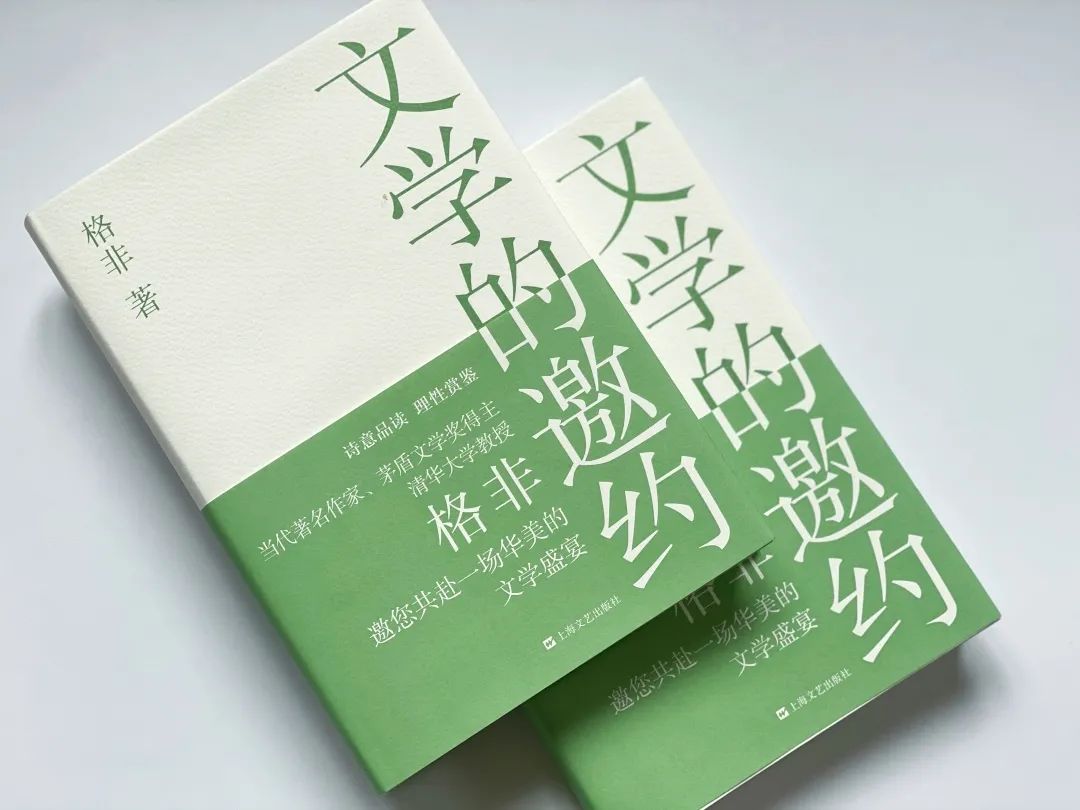
《文学的邀约》
格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