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好看的间谍小说,少不了英国国宝级作家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这部1963年出版的作品令当时依然从事情报工作的文坛新人勒卡雷一举成名。2005年,《柏林谍影》荣获英国推理作家协会评出的“五十年最佳”,足证其经久不衰的魅力。
一代代读者为《柏林谍影》的故事洒泪唏嘘,勒卡雷本人也始终牵挂着那段谍报往事。在八十五岁,勒卡雷推出了该书的续篇——《间谍的遗产》,重回柏林的寒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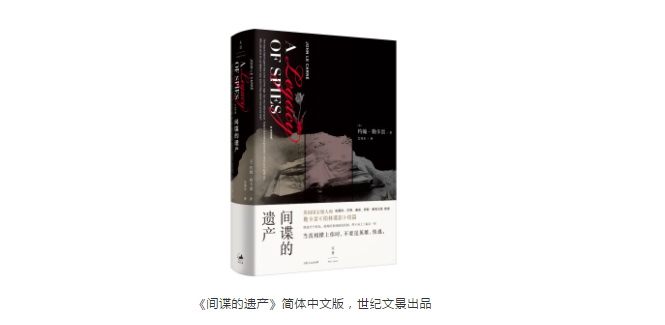
重回起点的史迈利传奇最终章
《间谍的遗产》追随史迈利爱将彼得·吉勒姆的视角展开。故事开篇细数吉勒姆错综复杂的家庭背景与加入情报局前后的往事,与勒卡雷1958年处女作《召唤死者》的第一章“乔治·史迈利简史”遥相呼应。这位挂靴老间谍在法国的安逸生活被一封密函打断,不得不连夜赶往伦敦的情报总部(又名“圆场”)报到。沧海桑田,圆场已从“造型浮夸的维多利亚风格红砖建筑”搬至“泰晤士河畔的某座怪诞堡垒”,圆场的旧人也已散落各处,踪影全无。
然而,过去对当下投下的阴影无可避免。在咄咄逼人的新一代圆场法务面前,已生华发的吉勒姆作为他们唯一能联系上的元老,作为关键证人(或者说,替罪羊)被推到一场一触即发的诉讼前。这一次,吉勒姆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昔日同僚的后裔——其父母有着老一代情报员无法忘记的名字:利玛斯与丽兹。
《柏林谍影》中失控的情报事件要追溯到近半个世纪前,但忠实情报官与爱人命陨柏林墙下的惨状依然历历在目。是什么导致了两人的死?是圆场故意弃子,还是另有隐情?故人的鲜血已在历史长河中锈迹斑斑,时代的伤痕却在个体的身上诉说着全新的伤痛。两个冷战遗孤意欲拿起法律的武器,向圆场提出巨额索赔。事件的关键人物史迈利下落不明,他的左右手吉勒姆必须在官方记录与私人记忆的交叠与错位之处,在见证了往昔血雨腥风、而今荣光不再的安全屋中,去试图回答:曾经的正义在当下语境中是否依然成立?老一代的行为是否可以得到下一代的理解?当真相撵上你时,是逞英雄,还是快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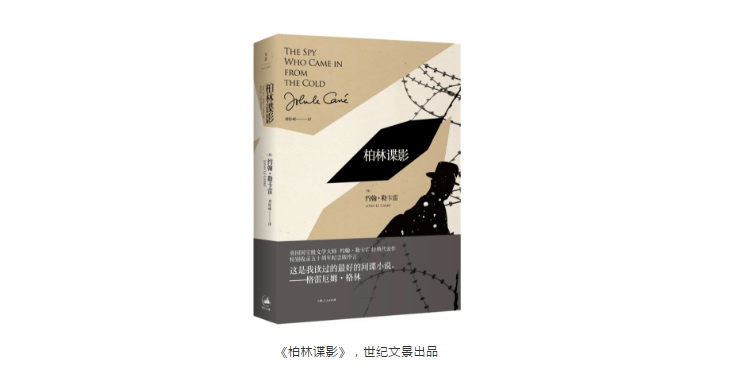
以下内容皆真实可信,我将尽己所能,陈述我本人在代号为“横财”的英国欺诈行动中所饰角色的亲身经历。该行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针对东德情报局(斯塔西)展开并执行,行动导致我曾合作过的最杰出的英国特工死亡,该英国特工甘愿为之献出生命的无辜女性,亦随之香消玉殒。
——《间谍的遗产》
《间谍的遗产》是史迈利系列的第九本,也是大概率的收官之作,用勒卡雷的话说就是:“毕竟,史迈利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勒卡雷献给粉丝的礼物
1958年,二十六岁的大卫·康威尔在伦敦西区柯曾街莱肯菲尔德大楼三楼一间狭小的里屋中,创造出“约翰·勒卡雷”这个笔名,与之同时诞生的,还有乔治·史迈利这个英国人。史迈利“五短身材,臃肿体态,外加一副温顺脾性”,和007特工之类潇洒多金的间谍形象搭不上边(用安恩女士的话,便是“普通得令人心动”)。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日后深入人心,被誉为“战后小说中最丰满、聪明、吸引人”的角色之一,常立于世界文学经典人物之林。
勒卡雷基于情报局的工作经历,虚构出一家情报机构,因其地处剑桥圆场而取名“圆场”(Circus)。在英文中,圆场也有“马戏团”之意。“还有什么比‘马戏团’更适合形容一群精于表演艺术的间谍呢?”勒卡雷说。
在任何一场审讯中,否认就是临界点。不要在意之前的谈话有多么礼貌客气。从否认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就一个秘密警察的普遍水平而言,否认可能会招致报复行为,因为秘密警察普遍都要比他们的审讯对象蠢一些。与此相对的,那些老练的审讯员一旦发现面前原本开着的门突然砰的一下关上了,并不会选择马上去进行正面击破。他们更愿意重整旗鼓,尝试从不同角度接近目标。
——《间谍的遗产》
《间谍的遗产》中,勒卡雷书迷熟悉的配方随处可见,让人耳熟能详、爱恨交织的人物也一一登场:吉勒姆、普莱多、米莉、海顿……普莱多在暗杀变节者后何去何从?史迈利与卡拉的纠葛如何落幕?书中 “彩蛋”甚多,只待有心人去发现。
交稿令人神伤,提笔满血复活
《柏林谍影》的出版令勒卡雷名声大噪,但他作为间谍的身份也随之暴露,好在文学造诣过硬,让他得以靠写字营生。迄今为止,勒卡雷已创作小说二十五部以及一部名为《鸽子隧道》的回忆录,文学影响力早已超出了类型小说的范畴。《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认为:“勒卡雷早已不是类型小说作家,他很可能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