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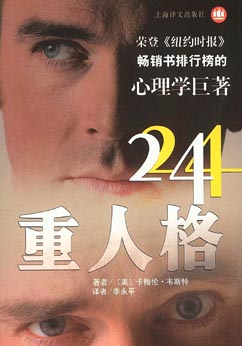 对于卡梅伦·韦斯特来说,他的躯体不啻是一家“伤心旅馆”,他的24位“分身”或者说“他我”,一个个提着行囊来到旅馆,入住他心灵中那一间间早已客满的房间。有些只逗留几天,然后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有些一住进来就赖着不走,大有在此终老、与旅馆共存亡之势。他们盘踞着韦斯特的心灵,接管着他的身体,结果韦斯特变成了24个人。也就是说,当韦斯特操着低沉浑厚的男中音与你侃侃而谈之时,他极可能会以一种童稚的嗓音说道:“我想尿尿”。甚至,在与妻子亲热时,他也会突然变成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对此,你会不会惊骇莫名,满以为自己大白天撞见了鬼? 对于卡梅伦·韦斯特来说,他的躯体不啻是一家“伤心旅馆”,他的24位“分身”或者说“他我”,一个个提着行囊来到旅馆,入住他心灵中那一间间早已客满的房间。有些只逗留几天,然后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有些一住进来就赖着不走,大有在此终老、与旅馆共存亡之势。他们盘踞着韦斯特的心灵,接管着他的身体,结果韦斯特变成了24个人。也就是说,当韦斯特操着低沉浑厚的男中音与你侃侃而谈之时,他极可能会以一种童稚的嗓音说道:“我想尿尿”。甚至,在与妻子亲热时,他也会突然变成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对此,你会不会惊骇莫名,满以为自己大白天撞见了鬼?
不,这不是活见鬼,而是事实,是一个叫韦斯特的美国人的亲身经历。韦斯特是心理学博士,同时又是一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简称DID)患者。患病时的韦斯特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与他哥哥经营着一家蛮不错的公司,也有了温柔贤惠的妻子、聪明可爱的孩子。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一切都令人满意,甚至叫人羡慕。然而,有一天,情况突然起了变化:韦斯特仿佛恶魔缠身,变成了好几个性格、习性和记忆各异的孩子或小伙子,嘴巴里发出来的是别人的声音,驾车外出却找不到回家的路,还在一个神秘声音指使下屡次割伤自己的手、抓破自己的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疯了吗?
原来,这一切与韦斯特的外婆、母亲和一位陌生男人有关。在韦斯特小时候,他们都曾强迫他进行过某种性行为。当时的韦斯特没办法应付性虐待,而为了保护自己,以免让自己沉溺在这种恐怖的经验中,他就必须让自己跟这些事件“分离”开来——这就产生了所谓“人格分裂”。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自我(分身)暂时带走了有关虐待事件的记忆和感受,但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在韦斯特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多年以后,这些分身,连同当时的记忆和感受,像是一根根从大海淤泥深处翻腾上来的腐草,开始浮出水面,随波逐浪,时沉时浮,于是韦斯特也就有了不同的“我”。
为了治病,韦斯特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远走他乡,挈妻将子搬迁到加利福尼亚州。然而,对于韦斯特来说,这里并不总是阳光明媚,妻子开始与人频频约会,孩子对于自己的病情也并不是一无所知……屋漏偏遭连夜雨,韦斯特该怎么办?他的病有治愈的希望吗?如何应付棘手的家庭危机,如何面对幼小的孩子……这一切都是迫在眉睫不容回避的问题。
韦斯特遭受人格分裂痛苦折磨数年之久,其间的人格裂变、身份转换、恐怖、忧惧、犹疑、软弱、消沉、绝望等滋味,决不是非亲历者所能体会。如今,他将这番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著作成书——《24重人格》(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作者就是书中痛苦的主人公,心理学家同时是精神疾病患者,正是这种似乎不可能的事实赋予了本书任何一位漂亮女子都无法具有的魅力。一些心理学家赞誉本书为“心理学巨著”,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有关人的生活,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梦魇般的隐喻,与每一个精神健全或不健全的人多少都有点关系。病是世界的譬喻,人人都在疾病中行进。不妨将本书与弗洛伊德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一并参读。
很难想象,一本心理学著作可以写得如此优美而又惊心动魄。24位分身,无论是第一个现身的“戴维”,紧张兮兮的“克莱”,温柔能干的“尘儿”,还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利夫”,一个个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涌身而出,栩栩如生。在书中,你可以体会到一个孩子在恐怖的驱逐下藏身深夜黑暗角落时那种欲呼无声的痛苦,可以触摸到患者掩面哭泣时从指间流淌下来的冰冷泪水,可以听到一群分身争辩时热闹而诡秘的叽叽喳喳声,可以看到分身们通过韦斯特的手写下的日记,其中的一个写道:“救救我”。当然,你也会因患者妻子伟大的爱而对她肃然起敬,因怀疑他们的幼子能否承受这一切而忧心忡忡,因患者最终满怀信心而欢欣鼓舞。这是一个有关心灵迷案的侦探故事,一段阅读时你没法无动于衷的苦难历程。
《24重人格》出版不久,就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先后在10个国家出版,《阿甘正传》的编剧即将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可以预期,一旦拍摄成功,它必定是一部比《阿甘正传》更好看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