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体验来得很强烈,以至于时间在那一刻好像完全停顿了。即使随后的时光继续流淌,我们的生活又重归原来的轨迹,但那些强烈的感受依然鲜活并将永远萦绕着我们。
十七年前,我最小的孩子受了重伤,危在旦夕。之前我就讲过这个故事,但我对它的理解一直在不断变化、深化。
这种理解的变化同样适用于我这些年来所讲述的关于环保的故事。在十七年前的那段日子里,我刚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濒临失衡的地球》,儿子的事故忽然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所以我开始重新思考一切,究竟什么才是我生活的重心。感谢上帝,儿子很快完全康复了。但是在那段苦难时光里i,我经历了两个变化:一是我发誓要将家庭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二是我发誓要将气候危机放在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位。
遗憾的是,在此期间,时间并未因全球环境恶化而停下脚步。环境破坏在一步步加剧,采取应对措施的需求也随之越来越紧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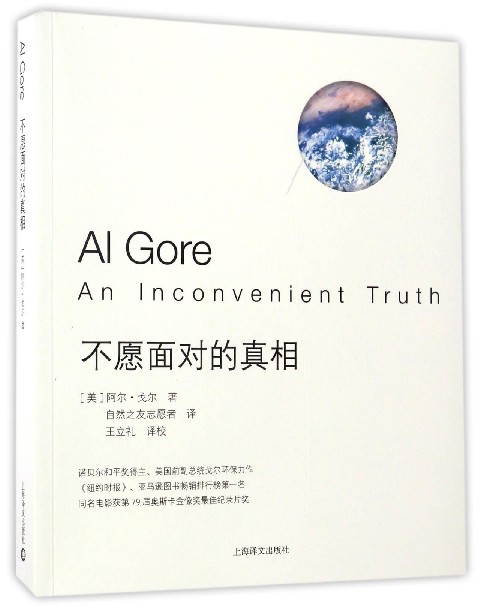
目前气候危机最基本的框架和当年相比并没有多少本质的改变。人类文明和地球之间的关系被一系列因素所共同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爆炸、科技革命,以及一种忽视今日行为对未来影响的思维。潜在的事实就是我们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冲突,结果其中最脆弱的部分崩溃了。
这些年来,我加深了对气候危机问题的了解。世界顶级科学家们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越来越严峻的警告。我阅读了他们的书,聆听了他们的演讲。随着危机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恶化,我越来越重视和关注这个问题。
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无论冰川融化还是雪山消亡,无论热浪袭来还是干旱入侵,无论在飓风的风眼里还是在灾民的泪水中——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已经留下了累积如山、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明自然周期发生了巨变。
我了解到,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至少还有一件不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了气候变暖,而且这种现象还在迅速加剧,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至于成为了全球性的现象。
在过去十四年中,我在生活的磨砺中学到了很多。蒂帕和我的孩子都成长了,两个大女儿都已经结婚,我们有了两个外孙。我的父母以及蒂帕的母亲都离开了人世。
1992年,《濒临失衡的地球》出版了。我竞选上了副总统一职,一干就是八年。作为克林顿-戈尔政府的成员,我有机会得以采取一系列新政来应对气候危机。
那时候,我亲身体会到国会如何抵制我们敦促他们做出变革,我失望地看到,自从共和党及其咄咄逼人的新任保守派领导人于1994年主导国会之后,反对之声越来越激烈了。
我组织并参与举办了不少活动来增强公民对气候危机的意识,争取他们对国会行动的支持。近几十年来,我也从中汲取了不少关于美国“民主对话”性质和质量的教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娱乐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所谓的新闻,独立的个体声音被公众言论排除在外。
1997年,我协助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会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次,全世界共同起草了一个奠基式的议定书来控制全球温室效应。但是当我回到美国时,却为争取参议院对该议定书的支持而陷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斗争。
2000年,我竞选总统。那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战役,最终以最高法院四比五的判决,结束了在关键选取佛罗里达州的计票。这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接着,我目睹了乔治·沃克·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当任的第一周他就违背了在竞选了作出的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而正是这一承诺使很多投票者相信布什真心关注全球环境问题。
选举过后不久,布什-切尼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决心,要反对任何控制温室效应的政策。他们竭尽全力地压制、削弱、甚至只要有可能就完全废除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甚至抛弃了布什竞选期间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承诺,宣称在总统看来全球变暖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随着新上任政府逐渐起步,我必须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毕竟,我没有工作了。这段时光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也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退后一步来思考怎么规划利用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我开始在田纳西州的两所大学里任教,并和妻子蒂帕一起撰写了关于美国家庭的两本书。我们搬到了纳什维尔,在离我们地处迦太基的农庄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购置了一栋房子。我步入了商界,并且开始经营两个新公司。我成为两个颇有名气的高科技公司的顾问。
我对这些新尝试感到非常兴奋,庆幸自己能在找到谋生手段的同时让世界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和合伙人乔尔·海厄特建立了“潮流电视台”。这是一个专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设计的新闻信息有线卫星网络,其运作的基本理念在我们当今社会很具有革命性,即观众自己可以制作节目,并且在过程中参与美国民主公众论坛。我和合伙人大卫·布拉德开了一家可持续投资管理公司,以此证明环境等可持续性因素能够完全整合到主流的投资流程,并且能给客户带来利润。
起初,我计划再次竞选总统,但是在过去几年,我发现了还有其他为大众服务的方式,而且我很喜欢这些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