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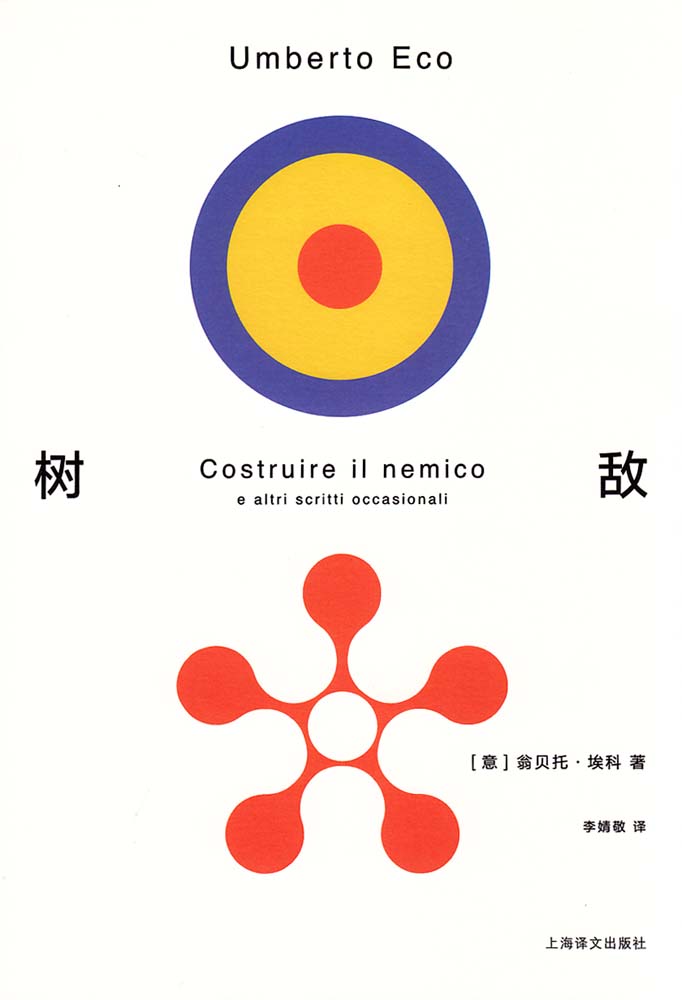 翁贝托·埃科,写小说的圣手,编故事的鬼才。 翁贝托·埃科,写小说的圣手,编故事的鬼才。
其名作《玫瑰的名字》早被译成几十种文字,销售超过1600册,其他小说皆以博学和解锁各种密码而闻名,如《傅科摆》,波谲云诡,枝蔓复杂,处处都有陷阱,处处都有历史的残片和智慧的火花。然而,写过五部畅销作品的小说家埃科,其实还是公共知识分子、符号学家、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埃科并非贪多嚼不烂,绝不会浅尝即止,他在每个领域都成就不菲,其杂文更因博学和深奥而让人印象深刻。
《树敌》一书,收文15篇,内容跨越古今、游走多重世界,将作家的多重身份融合于一本书中,从中我们既能看到学者埃科的哲学反思、文学惦念,又能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埃科的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有小说家埃科创作历程的蛛丝马迹,也有老顽童埃科以妙想奇思书写的生活滋味。
读埃科,即使没被说服,依然可能深深被折服。埃科的书常常让内行惊叹让外行悲叹,惊叹者多半仰慕埃科的博学,随手一捻,就是上下千年的文学公案;信笔一写,各种典故排山倒海而来。埃科能言擅道、巧舌如簧,喋喋不休得颇有巴洛克的繁复风格。他的书通常很挑读者,一旦读者缺少西方文学背景,埃科的博学就成为负荷,读不懂的人只能在他的书里载浮载沉,像汪洋大海里永远找不到方向的小鱼。
作为一位难得征服了欧美两大陆、跨越了雅俗两界河的人物,埃科的作品充满了热情与好奇。《树敌》是他2016年年初去世后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新书,内容庞杂,涉及话题大致可归为两类,一部分与文学相关,另一部分则为“偶谈”。在序言里,埃科透露曾想将书名命名为《偶谈集》。所谓偶谈,即命题作文,作者原本无意创作,是应他人要求就某一话题撰写的发言或文稿。这些话题能够促使或引导作者对某些会忽略的问题进行思考,相对于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奇思异想,这些由外界推动的反思往往更加丰富。《树敌》、《相对与绝对》和《火之炫》即可归之为偶谈。
埃科文风缜密、思维跳跃,读者不知不觉就掉进了一个高速旋转的陷阱,头晕目眩之后,好不容易爬出来,极不甘心,打开书本重新再读,又再次掉入陷阱。如《树敌》一文,埃科从在纽约坐出租车谈起,说到国家的敌人,而后过渡到敌人的体臭、外表丑陋,接着说起异教徒、犹太人,话锋一转又变到了歧视女性、女巫的由来,最后引用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说明树敌是人类天性的需求,话风再转,说到了萨特的《禁闭》,认为异类的存在让我们认清自己,基于此,才有了共存和忍让。仅此一文即可见,埃科既富于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又兼有后现代顽童式的洒脱,在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间的自由切换,使他的高深符号学理论沾染上世俗的活泼,也使他的通俗文学作品保有知识分子的睿智。
《寻宝》、《雨果,唉!论其对极致的崇尚》、《既入乡,且随俗》、《我是爱德蒙·唐泰斯》、《〈尤利西斯〉:我们的惦念》都是与文学相关的文章。《四十年后的六三学社》是理解埃科的重要文章,正是在“六三学社”期间,埃科接触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完成了成名作《开放的作品》,而后又有多部书籍出版,文章最后,埃科表达了对卡尔维诺的怀念。《电视女郎与保持缄默》、《既入乡,且随俗》和《关于“维基解密”之反思》等几篇文章则是对当今现实的反思,细细读下来,也让人看到埃科社会性的一面。
2008年《巴黎评论》访谈时问过埃科,他作品的主要魅力,是否源于门外汉读者因自己无知而感到羞愧,进而转化成对他博学轰炸的天真崇拜。对此,埃科说他一生写了100多本书,绝不仅仅是为了卖弄学问,相反学问渗透在他小说错综复杂的结构里,等着读者去发现。所以,对埃科感兴趣的读者,最重要的还是拿起书认真地读,那么博学的埃科就会引领我们至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纷繁世界,一如这本《树敌》。
Quotes
敌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文明在不断进步,敌人的形象也不能被消除。
树敌是人类天性的一种需求,就算是性格温和、热爱和平的人也不能免俗。
无非是把敌人的形象从某些人转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胁性且必须被战胜的社会因素上。例如:资本主义的剥削、环境污染、第三世界国家的饥饿问题等。
正如布莱希特所说,对于不公正现象的仇恨和报复便也会翻转脸面,变成正义。
随着不同民族间接触的增加,新型的敌人已不仅仅是处于我们的群体之外、在远隔千里的地方显示其差异的人群,还包括那些处于我们内部的人——我们之中的人。
由于异类的存在,我们才能认清自己,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共存和忍让。
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这个异类古怪到让我们无法忍受,由此,我们便把他放到敌人的位置上,也就构筑起了我们的人间地狱。
当萨特把三个生前互不相识的死人置于同一间酒店房间里时,他们中的一个参透了其中可怕的真相: 你们会明白这道理是多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儿没有肉刑,对吧?可我们是在地狱里呀。别的人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我们得永远在一起……这儿少一个人,少一个刽子手……他们是为了少雇几个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