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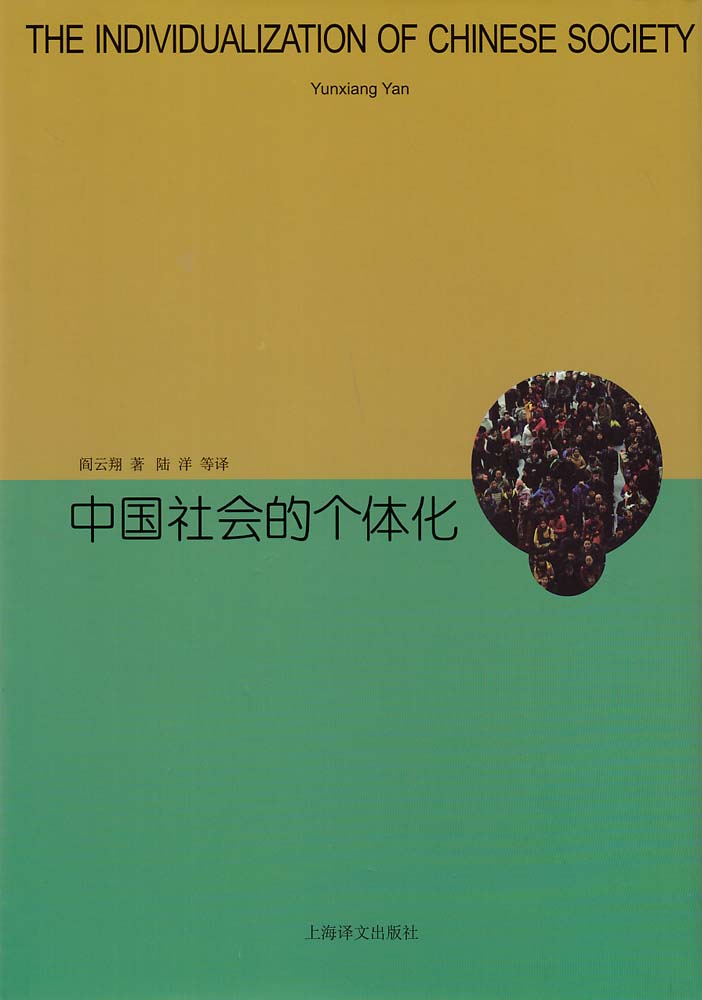 “我一代”:“松绑”的结果 “我一代”:“松绑”的结果
在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坐下来,同一些三十岁上下的人聊天,多半会发现,这群出生在改革开放策略实施之后的“八五后”一代,不论说起他们的生活,还是工作,都喜欢以“我”作为开头。你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毫不奇怪。然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表述,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是显得有些突兀的。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毛泽东时代的末期,虽然社会生活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到处充满着“不断革命”的激进氛围,而是多少显现出了一点生活的气息,但集体主义仍然是当时人们可以想象的唯一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不管怎么说,以“我们”开头的说辞,总是比以“我”作主语的句子,更具说服力。
当然,“我一代”(the“me-genera-tion”)的现象,不独出现在中国,它代表着具有个体主义倾向的人群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壮大。但是,或许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出现,比在其它地方显得更耐人寻味。因为传统中国在世界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社会,个体或“我”,在主流社会,从来不曾被当作一回事。而到了打破传统的共产革命胜利之后,“我”又似乎再次消失在了集体主义的大潮中:在公共集会和媒体上,只能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他们叫做“群众”,至于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喜好和向往,是没有人关心的,至少,那时的国家政权,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鼓励人们去关心这些有悖于“革命潮流”的存在。
但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切。在官方当年的表述里,这种给予社会和个人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政策,被称为“松绑”。这的确道出了真相。然而在中国人私人生活的细部,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嬗变,才迎来了这种让今天的年轻人喜欢得几乎难以自拔的西方“个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教授阎云翔的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就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作为张光直先生的高足,阎云翔教授年轻时,曾有过长达十多年的插队经历。当他试图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来解答这些疑问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田野调查地点,不是城市,而是他曾经在那里落户七年的所在:黑龙江省一个叫做下岬村的地方。选择这个地点,不仅是因为作者对当地村民的家庭情况十分熟悉,又有广泛的人脉,便于开展访谈和调查,更是因为,该村在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年里,各项经济指标,尤其是人均收入这一项,一直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因此令作者觉得具有典型性,适合作为民族志记录的对象。
村干部:政治资本的式微?
如上所述,中国社会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松绑”,也就是将原本属于社会和个体的权利,归还回来。在农村,这首先体现在“去集体化”的“分田到户”政策,它的官方表述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而这势必导致了那些在土地耕作集体化时代,承担着“派活”任务,也就是在农村基层掌权的村干部,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将田地耕作,也就是本村主要经济资源的生产和运作,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人们只需要和家人商量耕作计划,而不需要再看村干部的脸色,讨他们的欢喜,以便让自己在每天的工作中分到容易耕作的田地。而村干部在毛时代拥有的另一项权力——政治动员和对阶级敌人开展专政——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威力。由于社会不再被人为地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人民”和“敌人”,政治运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开展,对于过去出身地主、富农的人,以及其他的“阶级异己分子”而言,村干部在政治上也几乎不再具有威慑力。所以,情况看起来似乎是,村干部在改革开放到来后,很快被边缘化,而与这种权力式微相伴的,则是普通村民权利的提升。不过,阎云翔通过逐户的走访、调查和统计,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事实上,由于下岬村在过去相对比较富裕,它的包产到户政策,一直到1983年才正式落地。而作者从对各户家庭经济情况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可以理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1983年以前已经不在村里担任干部的人,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要明显差于1983年以后仍然在位的村干部家庭,有些甚至完全沦为了贫困户。而在后者,也就是仍然在位者的家庭中,富裕户的比例,则远超普通农户中的富裕户比例。从数量上说,则是占到了全村富裕户的一半有余。而在下岬村上千人口中,最多时也只有十几个人被选派担任村里的各种职务。
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了这些似乎不再“大权在握”的村干部家庭致富的呢?通过调查,作者发现,至少在1980年代,他们的致富门路,主要是运用自己的影响,安排家庭成员进入非农业部门(如军队、国营单位等)工作,以此获得远高于耕地所得的稳定的工资收入。换言之,尽管村干部不再拥有显形的强势权力,但隐形的权力或影响力,仍然使他们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此外,尽管不再有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需要,村干部也仍然是政权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由此,帮助这些人的家庭致富,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在国家眼里,应该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