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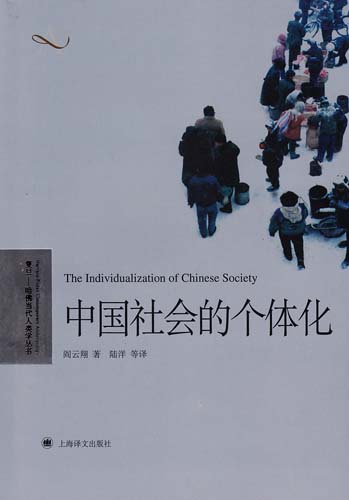 因为曾经长期生活在东北下岬村的缘故,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把东北下岬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的“标本”,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特别是长期不懈地探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分层、权力、家庭关系、消费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出现等领域的变迁,力图在观察、思考中努力拼接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路线图”。 因为曾经长期生活在东北下岬村的缘故,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把东北下岬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的“标本”,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特别是长期不懈地探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分层、权力、家庭关系、消费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出现等领域的变迁,力图在观察、思考中努力拼接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路线图”。
作为同样有过长期农村经历的笔者,对于阎云翔在本书中的许多陈述包括结论有着感同身受。比如分田到户后,“某些村民以前在集体制下面享受好处已经成为他们致富的障碍”,因为这些“出身好的普通农民忘了怎么侍弄庄稼”;一些“成功的个体利用炫耀性消费来博取社会地位”;通过分析比较“几代农村青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日益增长的反权威的情绪”;“消费主义政治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只能是越来越重要”……
毫无疑问,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重要条件。在下岬村,由于分田到户,原来集体劳作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耕作,传统意义上的基层约束组织权力被大大削弱,由此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解放,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家庭在分田到户头两年便迅速解决了口粮短缺问题,财富终于开始积累。最明显的标志当是,农村婚嫁出现了极其鲜明的物质标准——“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这种标志又不断更新变换,时至今日,期待以更为丰富的物质方式来彰显结婚喜庆的现象仍旧颇受社会推崇,而在过去,像这样的个体化表达,必须时时提防被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农村分田到户,打破了传统约束机制。农村改革实际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终于可以为自己不再饿肚子而心甘情愿地汗流浃背。但是,这一步是否真正促成了农村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则有待商榷。
囿于传统文化,农村关系错综复杂,有血源和亲情因素,也有姓氏和地域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人无论走到哪里,总喜欢以地域拉老乡,以姓氏拉本家等方式套近乎。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关系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放在农村,由于族系和姓氏的不同,往往导致势力差别。如此,个体社会间平等博弈制约的重要社会标志,往往被家族姓氏等关系所缠绕乃至覆盖,其结果亦可想而知。
至于阎云翔在书中所指,一些村干部不再像大集体时代,那么受到村民的爱戴与尊重。理论上,过去的权力架构确被打乱,村干部对村民的直接约束权力降低。但也应看到,这并不必然代表村民对村干部监督约束权力的“彼”消“我”涨。众所周知的是,“村官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下岬村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我们这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而言,这个标本显然难以包罗万象,其个体化的某些结论难涉被拔高之嫌。
顺便提及的一件事是,去年10月,当黑龙江的农民刘贵夫面对媒体说一年赚二三十万很轻松时,非但未能激起公众的共鸣,反倒引发社会的一片嘘声。事实上,刘贵夫是农场职工,当然算得上是农民,其承包土地多达30公顷,全部耕作由一家三口机械化操作,这样的收入倒也算不上有什么意外。但问题恰恰是,相较于全国9亿农民,刘贵夫到底有多少代表意义呢?想必,东北下岬村的个体化“路线图”的价值瓶颈亦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