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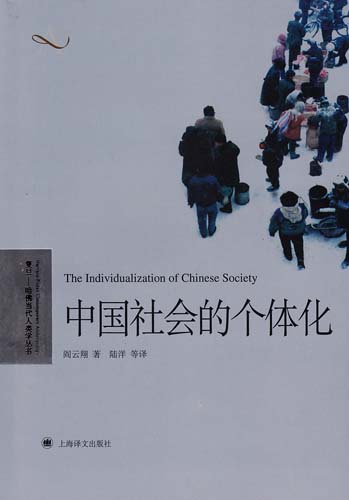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如今,说一个人有个性,通常是一种赞誉,而在不久之前,国人还不太习惯这样称赞别人,更不习惯接受这样的称赞。个人不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有时甚至还通过相当夸张的方式,人们也毫不迟疑地相信个人能通过努力改变其命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已宣告完成,很多人尚未充分意识到这是多么革命性的改变。
虽然阎云翔所主要选取的只是黑龙江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其中发生的变化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个体不再愿意为集体和家庭的延续而牺牲自己、在公共生活的真空中追求个体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年轻消费一代、年轻女性对家庭等级制度和代际权力关系的挑战……凡此等等,都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相似性让人感到历历在目,因为这一切事实上也是三十年来我在老家农村所经历和看到的情形。
个体权利的苏醒,最初源于权威的崩溃和撤出。我出生于1977年,恰好经历了这一过程:幼年时母亲还要每天出工去挣工分(这是集体时代的遗留),后来虽然抓阄分地,但在我十岁以前,村里的打谷机等农业器具仍是公共的,存放在集体的社场;八十年代中的乡村干部也仍能依靠其政治资本享有一定的个人威望,至少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为了进村办企业而请他们吃饭。然而逐渐地,一切都开始崩塌:社场慢慢倾圮成一堆废墟,最后平整为土地;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也不会再去给乡村干部送礼,有纠纷时也不再理睬他们的调解;年轻人既不愿务农,更不在意任何权威,他们想的只是离开这个困住他们的村庄,去追寻自我实现。将年青一代与其父辈相比较最能醒目地突出这一变化:他们不仅讨厌农活,不像父辈那样对乡村干部有一定的敬意,甚至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乡村干部。
这一幅图景,如今回想起来错综复杂、交替进行,但其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我”自己的发展和权利。只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是好事,而另一些人则更多看到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尚未确立——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如今的年轻人“没规矩”,他们更多地和自己情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玩,喜欢平等自由的气氛,而无法适应某些繁文缛节的场合中对身份秩序的强调,很多年轻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对乡村社会交错繁琐的家族谱系敬而远之,有些远房亲戚因为见面不多,甚至如何称呼他们本身就成了一件头痛之事。
一层隔膜
阎氏虽然在下岬村生活了十多年,但作为一个插队落户知青及后来的社会学家,他的身份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外人”,这使他一直能清醒地进行“参与式观察”,社会学家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要将普通的生活场景“去熟悉化”,这样才能发现意义。在《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两本著作中,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对乡村社会运作和变迁的敏感及理论素养,其细致入微令人印象深刻。但正如本书所显示的,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像是把这个乡村放在手术台上解剖,而甚少去体察乡村社会某些特定概念对人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我们乡下,固然人情往来也越来越多显示出礼物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理性算计的一面,但村里的舆论仍能有效地施加一定的压力。人们评论的用语也耐人寻味:该请的不请或送得太少,都被称为“不做人”,而人们也确实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招致这样的批评(至少对自己的行为能自我辩解),因为在乡村社会里“不做人”意味着别人都不愿和他来往。即使年青一代不太在乎,但也不能完全无视。“不做人”的评判是一种传统概念,它在新的社会变迁中仍顽强地留存下来,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在一定尺度内理性计算(太过了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或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失,也即社会资本损失),而且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些人的立身之本——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把“会做人”的社会评价看得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对他们来说,被看作“不做人”是极大的耻辱。这中间有一个平衡点。与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对“过日子”、“冤枉”、“讨说法”等概念的洞察相比,阎云翔似乎对中国农村中的人生理念有一层隔膜。
不可否认,这里有许多观点有他独到之见:对礼物、私人空间的重视是他此前就曾阐述过的,他也格外重视和强调年轻女性(尤其是她们作为儿媳妇时)的作用,也注意到家庭中儿子对媳妇的支持。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其原因之一也在于娘家比以往更重视女性了,陪嫁的嫁妆和对夫家的要求也因此水涨船高。他也没谈到女儿对女婿的包庇,而这在我们乡下同样是常见现象,或许对他来说这无法解释为“对父系权力的挑战”,但同样表明亲属关系的扁平化,而年青一代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受“现代爱情观”影响的结果,这种浪漫的爱情观在个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