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拉斯的《诗艺》在欧洲古代文艺学中占一个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上承亚理斯多德的《诗学》,下开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和古典主义文艺理论之端,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文学创作,尤其戏剧与诗歌,具有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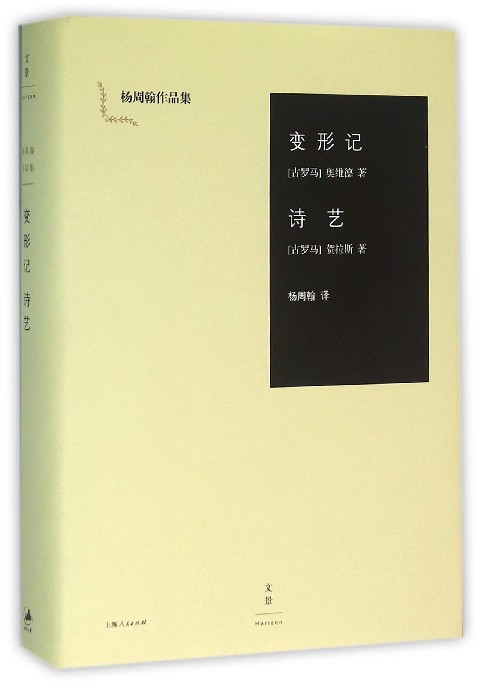
贺拉斯(O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年)生于意大利南部一个获释奴隶家庭。他父亲略具资财,送他到罗马受很好的教育,其后又送往雅典去学哲学。内战时期,贺拉斯在希腊参加共和派军队(公元前42年),共和派失败,他回到罗马。这时他父亲已死,田产充了公,他谋得一个小官,并开始写作。公元前39年由维吉尔介绍,他加入了奥古士都的亲信麦刻那斯的文学集团,约六年后,麦刻那斯在罗马附近赠送他一座庄园,他便在庄园与罗马二地消磨了此后的岁月,生活宁静。他的创作(抒情诗、讽刺诗等)一方面表现他依附宫廷,歌颂奥古士都,一方面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态度。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生活哲学,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有节制的、适度的享乐。这种适度的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文学观点中。
他在许多诗作中阐述了他的文学观点,但是最集中的阐述是他的晚期作品《诗艺))。在这封诗体书信里,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写下了一些经验之后,今天读来也还有可取之处。
这封信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开始的七十几行中,作者提出了他的总原则:一切创作都要合乎“情理”;一部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结构要首尾一致、恰到好处;事物不断变化,所以允许创新,但创新不能超过“习惯”所允许的范围。(二)接下去二百行主要谈戏剧。贺拉斯一方面强调作家应有生活感受,另一方面又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剧种、人物、场景、诗格都应有一定程序;题材最好利用现成的,才容易为人接受,而在组织安排上可以出奇制胜,这样来体现首创性。(三)最后二百行又一般地谈论文学创作问题,贺拉斯特别强调判断在创作中的作用,一个作家要能判断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他强调了文学的开化作用和教育作用,文学要起教育的效果,必须寓教诲于娱乐,不仅要内容好,而且艺术也要高超,语言要精炼,允许虚构,以便引人人胜;为了引人人胜,形式(包括语言)必须仔细琢磨,必臻上乘而后已,错误难免,但诗歌最忌平庸;天才固然重要,但必须与刻苦的功夫相结合,而刻苦功夫更为重要;要善于听取忠实的批评,以便一再修改。
贺拉斯继亚理斯多德之后,主张文学摹仿自然,到生活中去找范本,诗人必须有生活经验、真实感情。他肯定文学的教育作用,主张戏剧宣扬公民道德,歌颂英雄业绩,写爱国题材。这些论点对贵族统治、铜臭熏天、道德败坏的罗马社会不失为一种针砭。罗马戏剧自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以来,每况愈下,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后半专以机关布景竞胜,不重内容,完全成为缺乏教养的贵族的消遣品,贺拉斯的主张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贺拉斯的总的倾向是保守中求创新。他不反对创新,但要求合乎传统。他不贬低罗马文学成就,但更主张以希腊为师。他不忽视内容的重要,但更注意形式的完美,他所提出的“判断是成功之母”主要指恰当地掌握并运用文学形式的各种因素而言,占了全信很大比例。他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形式允许创新,但他更强调形式与形式不可相互混淆。这些论点反映了作者对缺乏素养的作家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罗马奴隶主文化的衰竭。 贺拉斯对诗歌的崇高任务、对生活的肯定、对罗马国家的高度评价等论点,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与评论家。他的理性原则、克制和适度的原则给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提供了依据。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在贺拉斯的启发下提出理性来反对封建的不合理,同时提倡克制,对王权作一定让步。贺拉斯主张借用古代题材、英雄业绩进行创作,深为古典主义剧作家所赞同,以此来鼓起当时所需要的公民热情;他们由此进一步同意并引伸了贺拉斯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戏剧形式的主张。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十分强调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也推崇贺拉斯,贺拉斯的“寓教诲于娱乐”的主张正符合他们的要求。但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崇尚感情,贺拉斯的影响就大大减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