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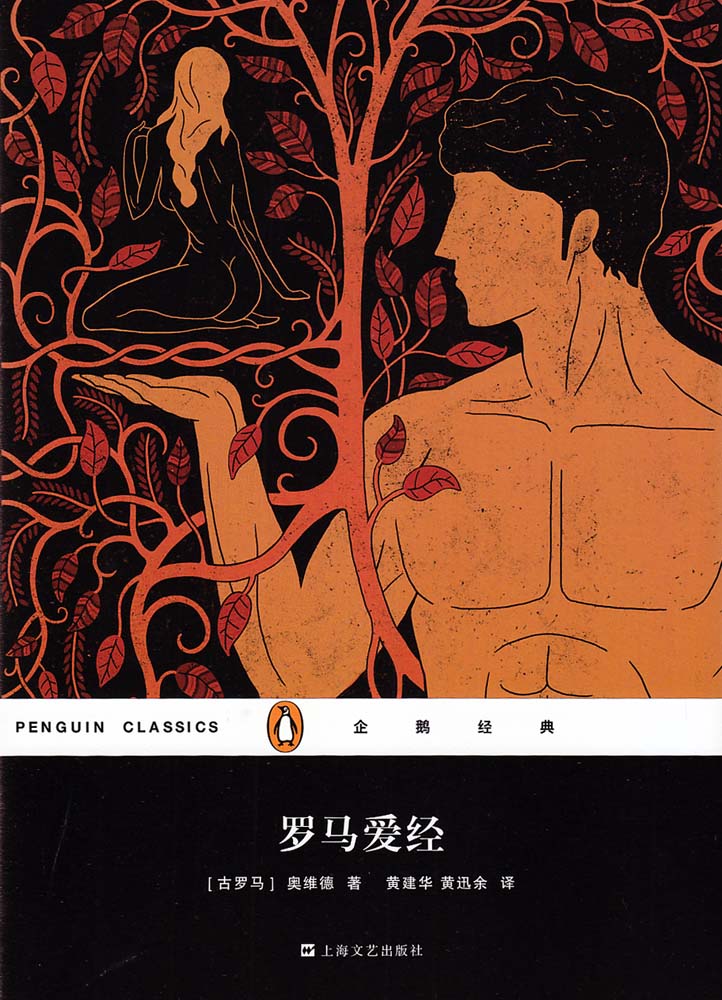 我偕小女迅余译完此书之后,出版社来函嘱托,要写一篇有分量的“学术性序言”。奥维德是古罗马的经典诗人,他的爱情诗篇几乎译成了所有西方文字,研究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著述,在西方世界里收集起来,如果不说车载斗量,也绝不会是个少数。可惜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研究家,无法为此作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于是就只好从译者的角度写上几行交代的文字。 我偕小女迅余译完此书之后,出版社来函嘱托,要写一篇有分量的“学术性序言”。奥维德是古罗马的经典诗人,他的爱情诗篇几乎译成了所有西方文字,研究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著述,在西方世界里收集起来,如果不说车载斗量,也绝不会是个少数。可惜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研究家,无法为此作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于是就只好从译者的角度写上几行交代的文字。
戴译与拙译
奥维德的名字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诗人戴望舒早就译出过他的《爱经》,而最近几年,许多家出版社一再把这《爱经》重印,有的印数还不少,可以说,这部描绘古罗马情爱的经典作品连同他的作者的名字,已经传遍中国大江南北了。
这次新译的《爱经》,虽则书名沿用戴望舒的译名,但和他所译的《爱经》却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是分量上的不一样。新译本汇集了奥维德三部主要的爱情作品:《恋情集》(《Amores》)、《爱的技巧》(《Ars armatoria》)、《情伤良方》(《Remedium Amoris》)。戴望舒只译了中间的一部,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吧。
其次,新译本作了分篇、分段或分首的处理,还加上了小标题,眉目清晰得多。这都不是译者的妄加,而是接纳了奥维德研究家的成果所致。为了翻译此书,我曾经参考过几个版本和法文译本,择善而从之,绝不敢随便抓到一本,便率尔移译。
再次,新译本的准确程度要略高一些,避免了旧译的一些疏误。我译此书到第二部分时,曾恭恭敬敬的把戴译本放在案头作为参考。平心而论,和二、三十年代的译品比较而言,戴译可以称得上是严谨之作,错漏的情况不算太多。但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局限,仍不免见到一些明显的误译。兹举一例,以为佐证,请注意在其下划线的文字:
戴译:“只有一个劝告,假如你对于我所教的功课有几分信心,假如我的话不被狂风吹到大海去,千万不要冒险,否则也得弄个地。”
新译:“如果你对我所传授的技巧还有几分信心,如果我的话不至被狂风吹到大海去,那我就给你这么一个忠告:要么就别去碰运气,要么就冒险到底。”
……
然而即使这样,我加的注文仍然达六百条左右。不是我的“学识渊博”,而是我受的诱惑太大,因为我手头的法译本,除了诗体本之外,都有极其详尽的注释,其中一套,著文达一千两百五十条,密麻麻的小字体印了八十余页。这不消说,是人家的研究成果,我如照译,一则会牵涉到版权的问题,二则其中许多内容也不是我国一般读者所必需(例如引证古希腊文的出处),于是我就拿不同的注释来个对照参考,再查阅几本神话辞典,自撰简短的注文。我这里不敢掠他人之美,我得坦率承认:如无法文译者所下的功夫,有些注释,我是无法去加的。写到这里,我不免对周良沛关于戴译的一段话产生了一点疑问:
“译者写了四百多条注文,在这本译本中,占了全书很大一部分篇幅,注文涉及古罗马的历史、传说、神话及那时政治、风尚习俗,显示了译者渊博的学识和做学问的认真。光读这些注文,也大有收益。”u
既然周先生还说“书也可能是根据法文转译的”,戴望舒大概不会不参考法译者的注释,如此一来,所谓“渊博的学识和做学问的认真”就势必要打折扣。因为,如果我尽量摘译或借用法译者的注释,要让注文占全书更大的篇幅,也并非难事。只是这样注来,读者是否会不耐烦,那就很难说了。
我这样提出疑问,并无贬抑前人的意思,而只是想还事物一个本来面目而已。尚希戴望舒诗歌的欣赏者(其实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鉴我,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