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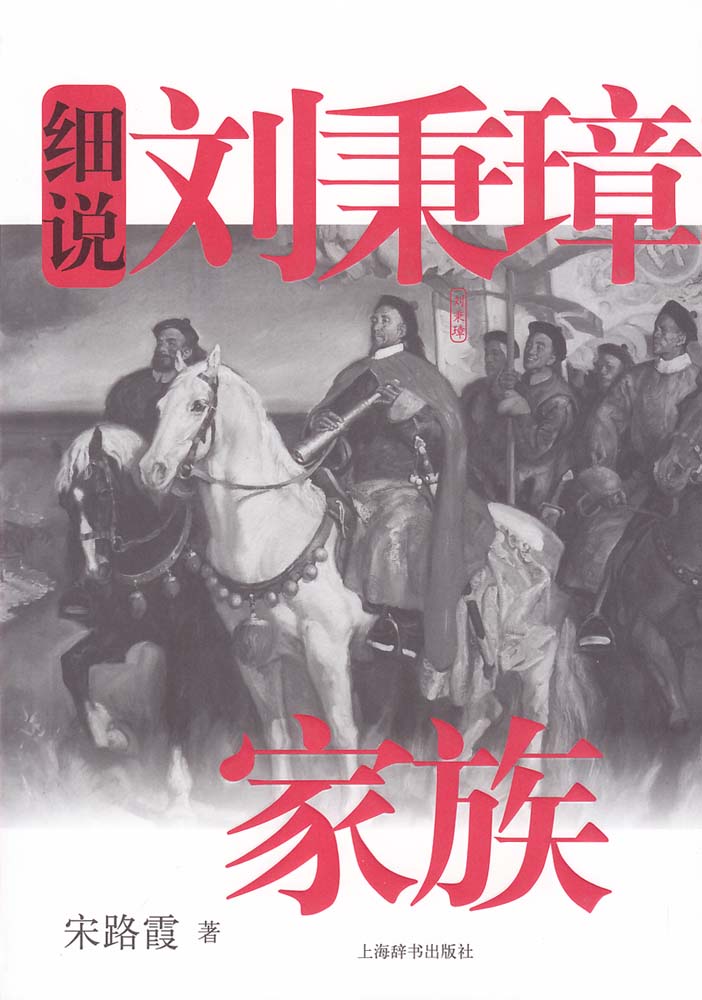 第一次听说刘家故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与如今已经101岁的周退密先生合作写《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 第一次听说刘家故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与如今已经101岁的周退密先生合作写《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
有一天我前去拜访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老先生历数上海民国年间的著名藏书家,其中着重说到了刘家藏书楼——小校经阁的主人刘晦之先生。顾老在新中国成立初亲自接收刘晦之先生的捐书,并亲自参与编目和整理工作,编制了厚达二寸的《刘晦之先生捐赠小校经阁藏书清册》和《庐江刘氏捐赠石刻拓本记目》,因此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刘老先生的藏书是按照《四库全书》的目录来收集的。做法是,一是要把“四库”中的“存目”之书收齐;二是力图收全列入‘四库“古籍的原刻本,并据此把四库馆臣们依照清廷的”思想“删改过的内容,再改正过来,恢复古籍的原貌。所以他的捐书中钞本很多。也就是说,刘老先生立志要以一己之力,编制中国第八部《四库全书》……顾老谈到这一点时,非常感慨地对笔者说:”真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胆识过人之士!“
此后,我开始留心刘家后人的消息。巧得很,有一次跟周退密先生讨论书稿时,他无意间谈起认识刘晦之先生的孙子刘笃龄。于是赶紧联系,请刘笃龄先生引领,怀着朝拜般的心情前去新闸路寻找小校经阁旧址。那时,院子东面的围墙还是高高的旧竹篱笆,杂乱的草堆里依稀可见一些零碎的太湖石,院子里的四棵广玉兰遮天蔽日。临街大门好像是木头做的,小校经阁的门窗还是老样子,四层住宅大楼外表依然气派、挺括,尽管里面已经是“七十二家房客”……
这次为写此书,为弄清细节,再去那里寻寻觅觅,已全然不同。虽然大门口挂上了静安区名人故居的牌子,但是院内的杂乱实在不敢恭维……然而这次陪同我前去的刘耋龄先生说,小校经阁能够保留下来没有拆掉,已经算是万幸了。此话属实,因为周围的老房子,包括海关的百年老钟楼都拆掉了,新式高楼如雨后春笋。
1993年《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出版后,为写《上海的豪门旧梦》,我与刘家后人交往的机会就多了,认识、结交了很多刘家后代,如刘善龄、刘永龄、刘延龄、刘松龄、刘桂龄、刘绳曾、刘德曾、刘荣曾、刘禄曾、刘宠曾、刘国瑞、刘诗群、刘远扬……他们提供了很多刘家史料、照片,刘远扬先生还帮助修复了很多老照片。从他们的回忆和描述中,可以看出刘氏家族精彩的沧桑往事,恰是中国百年大历史的浓缩和注脚,愈发放射出一种引人前去一探究竟、欲罢不能的诱惑。还有几位刘家上一代的老人如刘子益、亲戚孙曜东,他们一旦摆起“龙门阵”,动辄就是百年风云、十里洋场、豪门恩怨、陵谷兴替……尽管起初他们还有很多禁忌,并不情愿打开话匣子,因为十年浩劫“祸从口出”的教训还没忘却,后来经不住笆者的软磨硬泡,于是,渐渐地,这本《细说刘秉璋家族》就充满了他们的故事。
这期间常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如海外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笔者曾在华东师范大学多次听过他大会小会的演讲,他那亦庄亦谐、挥洒自如的“唐派散文”,令一帮热衷“胡学”的大学生、研究生无比崇拜。后来才得知,他老人家居然也是刘家后人,是刘家三房的外孙,他的母亲刘若霞是刘秉璋的三儿子刘体信的女儿,他本人还参加过呼吁保护小校经阁的活动,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至于刘家的老祖宗、四川总督刘秉璋,过去笔者只知道他会读书、会打仗,后经深挖、研究才知道,原来老人家还这么有人情味!关于杨乃武与小弊菜的案子,史料上早已经推倒重判、铁案如山了,而在刘秉璋的三儿子、著名清史专家刘体信的笔下,居然又起波澜……
刘家是—本大书,涉及清末民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收藏、教育、淮系豪门及官场人事等各个方面。小校经阁是刘家留在上海的一座丰碑,是一代名门望族精神生活的象征,也是民国期间文化人友好交往的一处见证。此书或许只是纸上谈兵,而眼下,保护好小校经阁这座沪上仅存的民国私家藏书楼,实乃任重道远。
感谢刘耋龄老师为此书的出版提供资助!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
愿年轻人从刘家的故事中得到启发。
愿老上海们抓紧时间,留下更多的历史真相。
宋路霞
2015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