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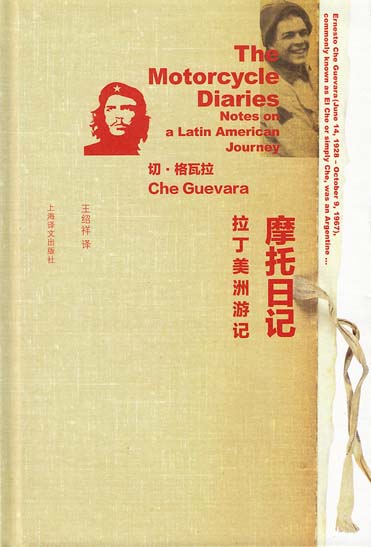 理想主义情怀与实干精神兼具,切·格瓦拉被很多人看成现代的堂吉诃德,与甘地、特蕾莎修女这样的圣贤一同照亮这个越来越缺乏本真和激情的浑噩世界。 理想主义情怀与实干精神兼具,切·格瓦拉被很多人看成现代的堂吉诃德,与甘地、特蕾莎修女这样的圣贤一同照亮这个越来越缺乏本真和激情的浑噩世界。
理想主义情怀与实干精神兼具,切·格瓦拉被很多人看成现代的堂吉诃德,与甘地、特蕾莎修女这样的圣贤一同照亮这个越来越缺乏本真和激情的浑噩世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贺绿汀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歌》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之一。它与诸如《铁道游击队》这样的老电影或是连环画一同塑造了游击队战士的威猛形象。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游击队只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被赋予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他们几乎个个是金刚不坏之身。他们是英雄好汉的典型,比梁山好汉还要牛逼。他们是黑白色的神话,让我们以为行军打仗是很好玩的事。而真正的游击队员会告诉你,真实的游击战哪有唱的演的那般轻松;能侥幸在枪林弹雨中全身而退,就是个奇迹了。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战斗期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他被杀害的前两天。他留下的日记本就成了我们得以了解真实游击战争的珍贵资料。尽管从字迹漫漶的原稿到西班牙文正本,经英译本再到中译本,经过了不止一次的转译,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和平状态下的人难以切身体会的战斗生活。翻阅这本记录,一切游击队的浪漫神话都还原成了充满艰辛的现实斗争。游击队队员并非个个都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神枪手,大多数人仅仅接受过最基本的射击训练,有时候连放八枪也打不中一个敌人,浪费了子弹还暴露了己方,真可谓“猪一样的队友”。他们都是“飞行军”吗?事实上我们的英雄常常在日记里抱怨队伍行进速度太慢,不仅是因为山高水深的自然屏障的阻隔,更多时候是因为要照顾行动不便的伤员,或是要背负沉重的给养物资。在格瓦拉被俘前的那些时日,游击队就陷入了被政府军包围而又与外界失联的困境里,行动迟缓,举步维艰,哪有半点潇洒可言。
这是一支由多国战士组成的游击队。即便是对于队伍中的玻利维亚人而言,这个国家山区的自然条件之复杂,也远远超出了他们日常经验的范围。格瓦拉日记中提到的第一个敌人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蚊虫:亚瓜蚊、赫亨蚊、马里基蚊、扁虱……它们所造成的伤害虽不足以致命,却给健康和士气造成不小的麻烦。首先造成游击队减员的不是敌军,而是难以估测的自然环境。格瓦拉对一起溺水事故作了如此的评价:“本哈明身体虚弱,天生的体质就与游击斗争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是他具有争取胜利的坚强决心。这场考验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因为他的体格和意志太不相配了。”这种看似“冷血”的笔调,读来亦有悲壮之感。在残酷的战争中,必须用理性来克服多愁善感,作为领导者尤其应当如此。没有心思去欣赏奇景,没有时间来咀嚼悲痛,唯一要做的就是向目标进发。
这是日记,不是小说,在记述日常生活的种种困难时,作者没有必要因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而省去一些重复的细节。我们或许会觉得,在他的战斗生活中,我们的英雄最关心的问题并不高尚,那是生存的最基本问题:吃喝。罐头食品早就吃完,也鲜有“自有那敌人送上前”的好事,游击队可谓是调动人类一切智慧来寻觅食物。如果根据这本日记开出一张游击队日常食单,肯定会相当壮观。对于每一次能吃饱肚子的饭,作者一定会重重地记上一笔。吃喝问题会引发人际关系问题。有人会因为口渴难耐而哭鼻子,影响部队士气。有人会在夜间因为饥饿难耐违反纪律,偷开牛奶罐头和沙丁鱼罐头,不管是当场被人发现还是事后被人发现,免不了要起纠纷和猜忌。这个时候,做领导的格瓦拉就要出面解决问题,向大伙儿解释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同志间的内部矛盾……这些人际纠纷往往同时还是国际纠纷,比如格瓦拉从古巴带来的几位老战友起初就不受玻利维亚人信任,格瓦拉还得站在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在克服人与天、人与地、人与人的矛盾之外,他还得克服自己——他在日记中坦言,自己也有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会挥刀砍坐骑,而他一直到被俘前都在与哮喘病作顽强的抗争。他的意志力确乎超越了常人,光是能在辛劳奔波中坚持每天记日记,就足以让我们钦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