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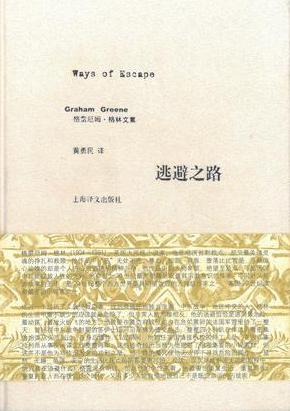 格雷厄姆·格林从小就是一个爱寻求刺激的人,为了逃避平凡枯燥的生活,他成了一名间谍。虽然他最初的间谍经历的确有点不同寻常,但真实的间谍生活其实并不如他从书里读到的那么刺激,多少让他失望了。 格雷厄姆·格林从小就是一个爱寻求刺激的人,为了逃避平凡枯燥的生活,他成了一名间谍。虽然他最初的间谍经历的确有点不同寻常,但真实的间谍生活其实并不如他从书里读到的那么刺激,多少让他失望了。
于是,首作便获得成功的小说之路,又成了他逃避枯燥的选择,尽管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平顺。
“1929年至1978年是一段漫长的工作生涯,”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写道,“不过在我考虑退休以前,我与自己有个约定,战后我的雄心壮志就是写一部没有常规暴力的间谍小说。”何为“常规暴力”的间谍小说?说白了就是缺乏冒险和传奇经历,没有香车和美女的间谍活动的日常生活:男人们每天到办公室朝九晚五地坐班,上班也是蹲守在格子间分析文档和解码电文,毫无危险性的例行公事,像其他平庸而枯燥的职业一样。
真实很乏味
这根本不像格林的间谍小说中描述的情节,但却是他真实生活的模样。他在《逃避之路》中提到,二战期间他在情报部门工作,先是西非,后回到伦敦,“工作中很少遇到刺激或传奇事件”。如果我们把格林小说中那些惊险的间谍遭遇与他多年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的经历对照,很容易就误认为他的生活就如他小说中写的那样,或者借用他另一本书的标题《生活曾经这样》。我们自行给间谍赋予了神秘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总觉得他们生活中时时刻刻存在的危险加剧了他们工作的冒险性质,这种独特的经历给他们以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源。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传奇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捏造,事实上,“我面对的是档案、档案、无穷无尽的档案”,“没有传奇和暴力事件打扰我们:只有封闭生活导致的某种无聊和厌倦”。
写作是欲望,是逃避——《逃避之路》
1929年至1978年确实颇漫长。1904年出生的格林,在牛津大学读书,学习历史,写诗歌,曾短暂地加入共产党——关于这段经历,他在《逃避之路》里满不在乎地说起18岁时当过四周共产党员,但就因为这段短暂的经历,1954年从波多黎各转机时被驱逐出境——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在《泰晤士报》当夜间编辑,白天写小说。1929年时,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内向的人》,这本书的成功激发了他当作家的梦想,他辞去编辑的工作开始专心写作。可他随后两本小说,《行动代号》和《黄昏的谣言》都失败了,两本书都糟糕透顶,任何批评都难以道尽它们的缺陷,这种打击一度伴随着他,让他觉得孤独,“我像一名被遗忘的伤员,感受到失败的凄凉和孤独”。
1941年,机缘巧合下格林开始为英国军情六处工作。他的上司是他朋友,也是后来被揭发的双面间谍吉姆·菲尔比。1944年,格林从军情六处辞职,但是他在游遍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的过程中,继续非正式地为军情六处提供服务,报告他旅行的所见所闻。
格林《生活曾经这样》的自传片段到他27岁便止了,而《逃避之路》则是在用另一种形式续写他27岁之后的生活,用回忆和散文的笔法,追溯他大半生的游历和写作之路。虽然格林说他游览过的那些地方成为小说创作的灵感源泉这种事情其实很少,但在阅读中我们总能从一幕幕场景里发现他游历生涯的蛛丝马迹。所谓“逃避之路”,有很多种意思:生活太乏味,所以需要全世界游历满足自己的冒险欲望,他去的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间谍生涯的枯燥,就用写作来丰满生活,小说中的故事比真正的间谍故事精彩得多。
欲望的追逐与逃避
1946年二战结束不久,格林发现因为长期被间谍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他对写作已经生疏了:“在整个战争年代里,我所从事的不是真正的写作—它是一种逃避,逃避现实和责任。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的小说是唯一的现实,是他的唯一责任。”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过去写作如何从一个情节进展到另一个情节,如何围绕不同的视角展开叙述,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写作突然变得艰难。这种深深的焦虑,甚至让他起了自杀的念头。
我总是对作家传记中关于写作的部分着迷。关注一个作家,只有关注写作本身才能让我意识到写作是怎么回事。格林的《逃避之路》中其实并无多少关于写作,格林把这本书写成了一篇篇旅游日记,其中某些片段更像小说中的场景。尽管他一再提及在他漫长的游历生涯中,其实并无多少传奇色彩。但是作为一名情报工作者,一名间谍,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引发一连串事件。他所经历过的历史场景,他所见证的改变世界的战争让读者渐渐意识到,我们正在朝他小说的心脏迈进。在格林的间谍小说中,总有一些人物和场景是和现实世界有交集的:《权力与荣耀》中墨西哥对天主教的清剿,《问题的核心》中荒原般的西非,《喜剧演员》中独裁统治下的海地,《恋情的终结》中二战时期的英国,《哈瓦那情报员》中哈瓦那的情报站,《文静的美国人》中冷战时期的越南,《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殖民地时期的刚果……这些历史性的场景一再涌现笔端,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现实世界的背景,也让他的小说脱离了单纯的娱乐消遣,增添了历史的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