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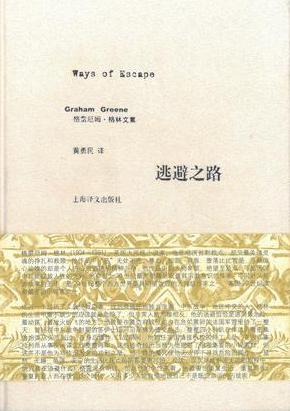 格林本打算在完成《生活曾经这样》时在二十七岁这里便“结束有关自己的记录”,正如他在青年时期的牛津岁月中变着法子屡屡尝试终结自己的生命一样。在用小刀割膝、吞服二十片阿斯匹林、甚至喝完一大罐硫代硫酸钠都不见成效后,发现哥哥的左轮手枪曾重新燃起过他胸中的火焰。在考量弹仓数量给足俄罗斯轮盘游戏六次机会仍未能如愿后,他还是兴奋地留下了一首名叫《赌博》的小诗,格林自己对此的解释是,这种种作死的另一面,“是经历一种超乎寻常的巨大喜悦,就像是黑暗肮脏的街上突然亮起了狂欢节的彩灯,我的心砰砰直跳,生活充满了无数的机会。”而这也无疑成为了他此后一生的注脚。在成为间谍、闯荡各种冲突之地,乃至伦敦大空袭时兴冲冲报名担任空袭瞭望哨的各个阶段,身背躁郁症的格林正是靠不绝的幻想与刺激生存下去,正如他事实上也无力阻挠自己继续出版《逃避之路》和《梦之日记》。格林坦言:“我还是品尝到这种回忆的愉悦。” 格林本打算在完成《生活曾经这样》时在二十七岁这里便“结束有关自己的记录”,正如他在青年时期的牛津岁月中变着法子屡屡尝试终结自己的生命一样。在用小刀割膝、吞服二十片阿斯匹林、甚至喝完一大罐硫代硫酸钠都不见成效后,发现哥哥的左轮手枪曾重新燃起过他胸中的火焰。在考量弹仓数量给足俄罗斯轮盘游戏六次机会仍未能如愿后,他还是兴奋地留下了一首名叫《赌博》的小诗,格林自己对此的解释是,这种种作死的另一面,“是经历一种超乎寻常的巨大喜悦,就像是黑暗肮脏的街上突然亮起了狂欢节的彩灯,我的心砰砰直跳,生活充满了无数的机会。”而这也无疑成为了他此后一生的注脚。在成为间谍、闯荡各种冲突之地,乃至伦敦大空袭时兴冲冲报名担任空袭瞭望哨的各个阶段,身背躁郁症的格林正是靠不绝的幻想与刺激生存下去,正如他事实上也无力阻挠自己继续出版《逃避之路》和《梦之日记》。格林坦言:“我还是品尝到这种回忆的愉悦。”
只是格林的“自传”,都只能勉强称得上“某种意义的自传”。一方面,或许秉承身为军情六处特派员的职业惯性,格林坚持岁月既属于自己又属于他人,要不侵犯他人——特别是与之有过牵连的爱人们——的隐私又记叙自己是不可能的,因此每每都要强调“专栏作家们最钟爱的那些往事片段仍不在收录范围”。就类型与内容而言,《生活曾经这样》更接近一种“精神分析”,《梦之日记》又是套上了“梦”之外衣的“一个怪人的三十年日记精选”,而《逃避之路》则来源于他重新为全集写的一系列序言以及与这些作品相关的构思和写作背景。另一方面,正如格林在《生活曾经这样》中承认的那样,他本人就是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因而不同于一般传记,你在了解他之前总会困扰于这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部分,多少想象的部分,多少等同于小说创作的部分。
格林并非那种在笔下开辟出全新疆域的类型,同样对技巧语言也没有过度的钻营,对他而言,创作是一种在尝试过自杀、网球、高尔夫、跳舞、航行等行为均告失败后的无奈坚持,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因此他的作品往往直接脱胎于彼时的生活经历与认识。这点上,《逃避之路》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大有裨益,你可以跟随他那种冷淡的调侃,来一道回顾他同文中角色贯穿始终的互文与发展。格林不喜欢许多自传作者醉心于“瞧,当年青涩的我有多荒唐”这种自卫方式,他骄傲地带我们回顾了他早年两部接近“玛丽苏文”的“二手浪漫故事”——《行动代号》与《黄昏留言》的创作始末,即便在被批为“是如此一个不屈不挠用心良苦的浪漫的作家……他达到了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顶点”后,他依旧神游物外到叫人无从下口:“这只是一个年轻而浪漫的小说家头脑中的白日梦,要经过无数年的沉思、内疚、自我批评和自我辩解,才能洗尽眼中那层迷茫的希望和梦想,以及那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 而且格林越来越觉得,把生活变得富有戏剧性,以此作为写作的材料,也未必就一定是二流作家的伎俩,毕竟“生活与作品,很难分清楚谁为因谁为果。有才的人总是很多情,他们写下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一般,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人生也会随之而来”。因此照搬他与凯瑟琳和亨利三角恋的《恋情的终结》可谓水到渠成,而后期格林基于人无法被救赎的不安写就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中,奎里又始终带着他自己的影子,挣扎于教俗两界的阴影之间。特别是格林既觉得像柯林医生这样从未陶醉于治病救人的无神论者“更接近上帝一点”,又同样记录下卡斯特罗无神论的那套还不如他在胸前画个十字更能抚慰一位丧子之父的“一次完胜”。这种反复碰壁又不断重来的期望,或许也正是已故翻译家傅惟慈偏爱格林胜过毛姆的原因所在,他觉得格林更通人性,说得出“爱的本质是有了解别人的愿望,但因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很快死亡,变成了痛苦、忠贞和怜悯”这样的话。
格林在书的开头详细记述了努达尔·格里格这位拥有传奇经历的挪威作家造访格洛斯特郡的前后,虽未明言,但谁都能看出努达尔之于格林的意义。这位怪咖同样总是容易“让浪漫占据上风”,在一次来英格兰交接银行库存时甚至幻想着得到隆重的接见,却因为等得不耐烦又撇下钱款自己叫车离开现场,最终还牺牲在了一次对德国的空袭行动中。在全书末尾格林也加上了一篇题为《那个人》的尾声,记录了成名之后总有一个神秘人冒充他身份的多年奇遇。可最后反而是正牌格林首先产生了疑虑:我是否一直是个骗子?我是那个人么?甚至是否可能是头脑中曾闪现过的任何一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