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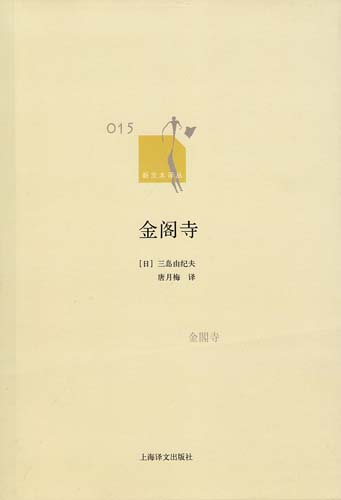 “数千万人生活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眼下我还是属于这类人。这种人生也罢死也罢,对社会都无关痛痒。” “数千万人生活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眼下我还是属于这类人。这种人生也罢死也罢,对社会都无关痛痒。”
“柏木教给我一条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的近道。乍看仿佛奔向毁灭,实则意外地富于术数,能把卑劣就地变成勇气,把我们通称为缺德的东西再次还原为纯粹的热能。”
“假使金阁被烧掉了,这帮家伙的世界将会被改变面貌,生活的金科玉律将会被推翻。”
辉煌灿烂的金阁,于翠松碧水之间耸立。去日本京都鹿苑寺参观的游人,都会为这绝美的景色所震撼。金阁集众美于一身:细节美、整体美、结构美、形态美、精致美、倒影的流动美等等。可是,1950年7月,寺里的一个小和尚故意放火,将国宝级的金阁焚为灰烬。现在人们见到的,已经不是15世纪时建造的那个金阁,而是复制品。根据这一事件,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了小说《金阁寺》,并因这部小说而扬名世界。
“我的脸是被世界拒绝的脸”
过去,对《金阁寺》的讨论,常围绕有关美与丑的哲学问题进行。现在重读《金阁寺》,书中对那个火烧金阁的小和尚的心理描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今那些校园枪击案的少年凶手,以及用自杀方式制造流血事件的年轻恐怖分子。小和尚也曾考虑过杀人,但后来认为还是烧金阁影响更大。
《金阁寺》系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就是那个日后火烧金阁的肇事者。在小说中,他的名字是沟口(在真实历史事件中,时年21岁的见习僧人林承贤纵火自焚,经抢救幸存,但烧毁了俗称“金阁”的鹿苑寺舍利殿)。
在学校里,沟口因为外貌丑陋和说话结巴,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不被他人所理解。他常感到自卑和自我嫌恶,认为“自己的脸是被世界拒绝的脸”。这些都造成他的心灵扭曲。他从小就爱看描写暴君的书,幻想自己成为暴君后,别人就都会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于是,他就可以把平日藐视他的教师和同学一个个地处以刑罚。他喜欢一个叫有为子的女孩儿,可后者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且还向家人告状,让他蒙受耻辱。于是,他“咒她尽快死去”。可见,他的幼小心灵,已经开始变得残忍。
灰暗渐渐生出了“光辉”
他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他自己尚未知晓的使命在等待着他。这种使命感,源于他内心深处极想成就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好彰显自己的力量,让那些认为他软弱可欺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他说:“数千万人生活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眼下我还是属于这类人。这种人生也罢死也罢,对社会都无关痛痒。”而他绝不甘心做这种人。
因为从小缺乏周围人的关爱,沟口在少年时代也“欠缺对人的应有的关心”。他已经习惯嘲笑和侮辱,以致别人的同情都不能合他的意了。到金阁寺做弟子后,他曾在美国兵的强迫下,用蹬着长统胶靴的脚去踩一个妓女的肚子。对此,他竟然一点儿都没感到于心不忍,原因之一是那个女人与有为子相同,对他连瞧也不瞧一眼。后来,他得知那女人当时怀有身孕,经那一踩就流产了。可是,他也并没因此感到后悔。不过,那时他还知道自己的感情“灰暗”,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可是,这行为后来“渐渐生出了光辉”,并感到“就像勋章那样挂在我的心底里”。可见,残忍的罪恶行为,在他脑中已转化成光荣的英雄行为。
深藏于内心的恶被激活
他从小就听父亲说,世间没有比金阁更美的东西。成为金阁寺的和尚后,他得以时常眺望金阁,甚至与其近距离接触。金阁在他心目中是美的象征,而他则陷入对金阁又爱又恨的纠结之中。实际上,他是在善行和恶行之间,在对人生的渴望和绝望之间挣扎。善良的鹤川曾给他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可随着鹤川死去以及邪恶的柏木施加影响,那一丝曙光很快就消失了。
柏木像一个邪教教主,有一整套理论和说教。沟口这样形容柏木对他的影响:“柏木教给我一条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的近道。乍看仿佛奔向毁灭,实则意外地富于术数,能把卑劣就地变成勇气,把我们通称为缺德的东西再次还原为纯粹的热能,这也可以叫做一种炼金术吧。随着对柏木的深入了解,我才明白他讨厌永恒的美。他的嗜好仅限于瞬间消失的音乐或数日之间就枯萎的插花,他讨厌建筑和文学。柏木暗示的,或在我面前表演的人生,其生存和破灭只具有同样的意义。在这种人生中,缺乏自然性,也缺乏像金阁那样的结构美。可以说,它只是一种痛苦的痉挛。而且我完全被它深深吸引,在这里认准了自己的方向,这也是事实。”从柏木身上,他看到一种“更黑暗的生,一种只要还活着就不停伤害他人的生的活动”。实际上,最初沟口对柏木心存反感,觉得他像魔鬼。可是,和他接触多了,沟口就在不知不觉间受其吸引。
在柏木的影响下,沟口心中渐渐萌生了一种与金阁决不相容的东西,“深藏于内心的那股邪恶力量被激活起来”。禅宗语录中,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临济录》中的“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能获得解脱。不拘于物而洒脱自在。”参禅者对这段语录自有多种解释,可对沟口来说,可能还是表面字义的腾腾杀气,迎合了他内心的残忍欲望。只有毁灭一切,才让他真正感到解脱。他曾希望战火将他和金阁一起毁灭。这个希望破灭以后,他就下决心亲自烧毁金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