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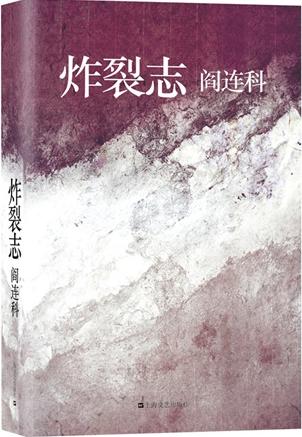 作家阎连科去年出版了他的新长篇小说《炸裂志》,据说出版社目前已卖掉七八万册,市场反应还不错。日前,复旦大学举办了“阎连科创作研讨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三十多位学者参加研讨会,既有对其文学成就的热烈肯定,也有直言不足的批评。 作家阎连科去年出版了他的新长篇小说《炸裂志》,据说出版社目前已卖掉七八万册,市场反应还不错。日前,复旦大学举办了“阎连科创作研讨会”,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三十多位学者参加研讨会,既有对其文学成就的热烈肯定,也有直言不足的批评。
阎连科在发言时语气诚恳而悲壮,认为自己六十岁前最多再写两三部长篇,担心自己江郎才尽,写不出新东西,甚至极言说这次复旦举办的研讨会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这么高规格的研讨会,希望专家多提意见,以促进小说创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认为,阎连科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他“能进得去”的作家之一。他相对更喜欢阎的早期小说,如《年月日》,“如果要选一批当代文学,这部作品一定在里面。”他尤其赞赏小说结尾的处理,一辈子历尽艰辛种玉米的老汉以自己的身体滋养玉米,玉米根须与他骨骼紧紧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令人震撼。
陈思和认为阎连科后来的小说《坚硬如水》是个创作上的转变,从写底层农民的生存欲望转变为写异化的物欲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扭曲,他加入了时代的现实批判。“很多人觉得阎连科他写欲望是有些过了,但他背后是有东西把他拉住的。”
中山大学谢有顺认为阎连科应该在写作与现实之间作出平衡。“当现实非常粗暴时,一位优秀的作家是否也需要用粗暴的方式去写作?其实,中国作家更需要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凝视。这种凝视所体现的温柔的力量或许更为强大。而急于阐述作家的观念,会导致作品的简单化,比如《炸裂志》把这个时代命名为‘炸裂’,非常生动精确,但在对中国现状作出揭露与总结时,阎连科认为金钱是造成当下社会黑暗乱象的原因,就有简单化的嫌疑。”
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则为阎连科的黑暗欲望写作说话,指出很多人认为阎连科的小说太暴力、太多仇恨,但作家未必要把自己束缚于现实主义的沉重包袱中,而是可以尝试任凭想象力飞翔超越。
辽宁师范大学张学昕认为,阎连科面对的是比巴尔扎克时代更复杂的时代。从《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到《炸裂志》,一部部作品呼啸而来,近三十年职业写作生涯,阎连科是盯现实盯得最紧的作家。骨子里有责任感和担当,在当代作家中是比较罕见的。他创作中不变的是他的骨感的、有痛感的、缺少美感的写作,带有批判、愤懑,这是他内心的一种扭结,与他生活中的待人宽厚造成分裂。他选择“荒寒”的与现实对峙的写作形式,这里恰恰显出阎连科写作对当代的意义。阎连科自己把他的写作命名为“神识主义”,强调作品的内真实,张学昕认为,阎的写作仍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里。
阎连科是中国目前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同时是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在复旦的演讲中,针对目前坊间流传的认为他是继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的传言,阎连科笑称,那只是个笑话,说说而已。但对其作品在国内出版有难度,“这不是我的选择,完全是命运的选择,自然的选择。”阎连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