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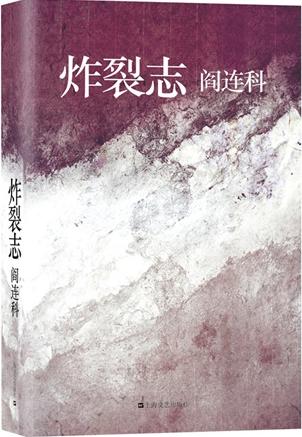 春节在家读完了阎连科的最新小说《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去年年终之时入选了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广受赞誉。但我以为,虽然这部小说算得上优秀,但还远称不上是杰作。它显示了阎连科面对现实发言的勇气,也折射出作者内心的焦灼和躁进。 春节在家读完了阎连科的最新小说《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在去年年终之时入选了多家媒体的年度好书,广受赞誉。但我以为,虽然这部小说算得上优秀,但还远称不上是杰作。它显示了阎连科面对现实发言的勇气,也折射出作者内心的焦灼和躁进。
毫无疑问,阎连科是当今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他最擅长的是用亦魔亦幻、亦真亦虚的故事来重构现实生活的残酷、真实和荒诞。这种手法被他称为“神实主义”。《炸裂志》用的依然是这种手法。
在书中,阎连科讲述了一个叫做“炸裂”的小山村,在三十年里飞速发展,最终成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故事。对这部作品,作者显然是抱有雄心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时,他曾自问:“一个作家是否可以通过一部作品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三十年,对当代人的人心进行审视?”答案不言而喻。
首先要说,用“炸裂”一词来隐喻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巨变,可谓精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家用长篇小说来“正面强攻”这如真似幻的现实生活,仅在2013年,我就读到了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值得鼓励。
但也许正是因为距离太近,沉淀太少,直面现实的勇气的另一面是匆忙上阵、力有不逮。余华的《第七天》读起来更像是新闻报道的文学化,贾平凹《带灯》的细碎也让我耐心全无。
而对于《炸裂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阎连科试图用其最擅长的“神实主义”来讲述中国的“炸裂”和“炸裂”的奥秘时,他的认识是粗糙的,叙事是失控的。在小说中,他描述权力和性的魔力时,细节精微,令人赞叹。但在对细节之后的人物性格上,他的聚焦显然不够,太过脸谱化,故事线索也有支离破碎之感。这种失控,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外明显,甚至使我一度丧失了读下去的兴趣。不客气说,这更像是一部完成度只有七分的半成品。
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个讲述“炸裂”故事的理想模型。最完美的模型也许是既有山村炸裂为大都市变化的外在勾勒,也有对炸裂之下人性的复杂、异化、幽微、温暖的深描。并且,对于文学来说,后者显然比前者更重要。如果前者是皮,那么后者就是骨。可惜,《炸裂志》在面对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的灵魂之“骨”时,失败了。
也许是三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了,“炸裂”得阎连科有点瞠目结舌,顾此失彼。为何会出现这种失控?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在两年多以前,阎连科在北京的住房遭到强拆,为此他发表了陈情信和《丧家狗的一年》的文章。陈情信和文章中讲到强拆时,满是无奈、焦灼、悲伤、愤懑,可谓百感交集。
也许正是因于此,阎连科内心充满焦灼和急躁。在写作中,他急于倾诉,急于将三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一股脑地说出来,最终不自觉地丧失了对故事节奏、细节的控制和打磨。现实伤害了他,最终影响了文学。
我担心,这本书终将会像中国三十年来所发生的许多故事一样,因为发生的太快了,最后也将被迅速地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