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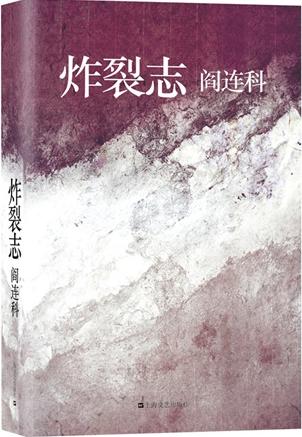 阎连科在谈话类节目上,曾经表示农民应该进城,应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如果将此观点对照《炸裂志》来看,那么农民不但应该进城,还应该将农村变成城市,以此来凸显我们当代社会的荒谬和悖论。 阎连科在谈话类节目上,曾经表示农民应该进城,应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如果将此观点对照《炸裂志》来看,那么农民不但应该进城,还应该将农村变成城市,以此来凸显我们当代社会的荒谬和悖论。
野蛮总是跟贫穷有关。“炸裂村”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贫瘠和穷困,而刁民孕育而生,他们不但完成了基本的温饱成为村中有办法活下去的人,逐渐也成为统领和占有这个世界的人。“孔明亮”靠扒火车致富的经历,颇有中国当代现实的意义,基本上来说,富人在穷人眼里永远充满原罪,不同的是中国这里发生的只是技术含量稍低罢了。
当村中的耕地荒芜,当街道两旁繁荣昌盛的商业区瞬间形成,当生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当所谓的贸易伴随着掺假和祸害环境滋生出来,人类得到的是欲望的满足,以及这之后的空虚。人类之所以在这个星球上孜孜不倦地折腾这么多年,除了满足眼前欲念还能找出其他理由吗?即便随之人类也发明出一些诸如“理想”、“道德”、“崇高”、“环保”之类的词,但这些也几乎都可以匍匐在欲望之下。
《炸裂志》有着一颗深入描写中国近年人心和颠沛社会的野心,但细究之时,它并没有给予指出欲望之河的源头和执着地去洞察这里荒诞的发轫之初,自然对眼下这种“炸裂”之态的形成也就缺乏了更深刻的解读。对于读者来说,掩卷之时只能“自治”和惘然。
此书将一个荒诞的并急速发展膨胀的村庄,通过一个野心家的村长、市长在使之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呈现了出来,这种直接进入事物运行核心的写法,当然是最能反映事物形成发展的角度,但也同时犯下了作家最喜欢的大而全、所谓彻底清算之类的毛病。放弃了小人物和周边细小变化的视角,成全了宏大、核心的叙事功能,这种不能说是失败,但的确可以看做眼下那些著名作家身上的一种顽疾。
在我看来,以个人的心念去热衷描写宏大历史和壮烈人物的特性,是中国作家动不动就露怯的重要理由。不是说那些宏大的历史和气吞山河的大变局不能去写,而是太多人尝试去描述和再现伟大的历史时会显得卑微和力不从心,至于那些小人物的琐事和日常生活中的破事,于当代文学版图中又显得过于凋败和冷清了。
无论是从阎连科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日光流年》、《受活》,还是在禁锢中得到另外一种关注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都能感受到作家的一种焦灼。这种焦灼与其说是一代人从内心到遭遇的必然心理动态,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工作的人和创造精神产品的艺术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神实主义”作为一个阎连科自己发明出来,并用来形容和概括自己的专用词汇,这个本来就是嫁接和杂交的名词,被堂而皇之地拥有之时,也是我们承认自身受到无法改变的限制的时候。“神实主义”迄今还是一个“虚妄”的概念,无论阎连科自己操练实践的那一系列的作品,还是他愿意将之拉上入伙的一众作家,都令这个词语既无法独立于后现代、魔幻现实主义(相反,在我看来它只是聪明和讨巧地利用了后者,而中国作家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身上吸取养分则是另一个话题了),也暂时看来不可能成为有效的、可追随的、自觉形成的一种文学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