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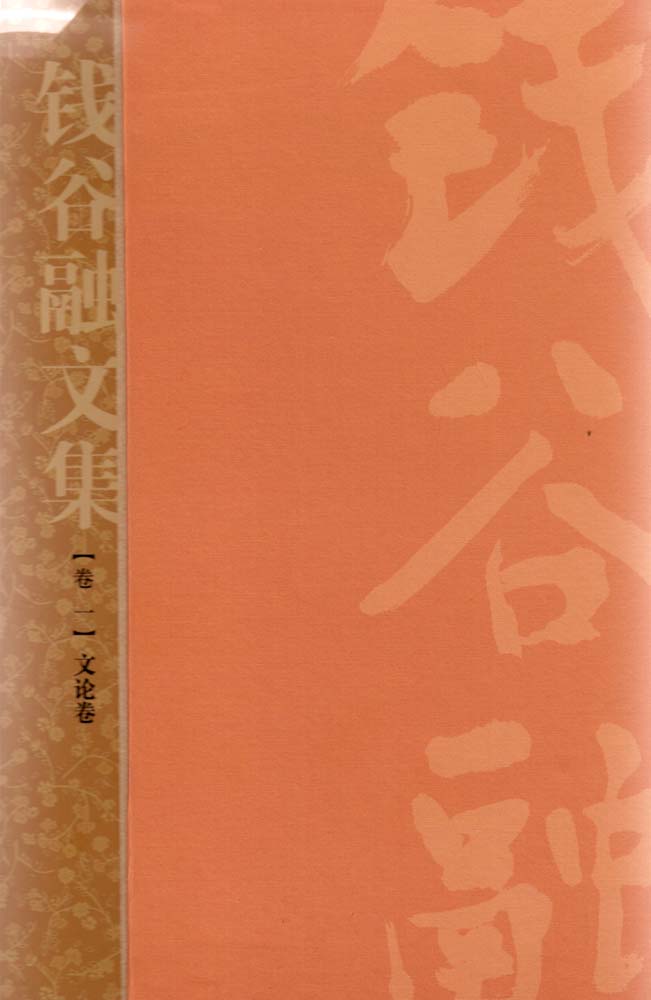 自由散淡如钱谷融先生,说“场面话”也不拘一格。在12月19日上海市作协举行的“《钱谷融文集》出版座谈会”上,面对与会者众星捧月般的夸赞,95岁高龄的钱谷融淡然道:“大家都讲我不无能、懒惰,都以为知道我。其实你们都不知道的,你们讲的都是不对的。” 自由散淡如钱谷融先生,说“场面话”也不拘一格。在12月19日上海市作协举行的“《钱谷融文集》出版座谈会”上,面对与会者众星捧月般的夸赞,95岁高龄的钱谷融淡然道:“大家都讲我不无能、懒惰,都以为知道我。其实你们都不知道的,你们讲的都是不对的。”
与其说是不领情,不如讲是钱谷融自由惯了,不喜欢条条框框的“限制”。他自言一生没做过学问,看东西全凭爱好。“懒惰”和“无能”,是他反复用来形容自己的词。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无能”大致因为他天性淡泊,不愿与人争胜;“懒惰”则是自认“无能”之后的选择,“因为无能,所以还是懒散些好,得过且过,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对钱谷融的这句口头禅做了“考证”。他说,现在有文字可查最早的出处是钱老发表于1998年5月4日的一篇文章,“他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第一次说自己‘无能与懒惰’,然后到了1999年6月1日,在一个对话录序里,第一句就说‘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陈子善说,这当然是自谦之词,因为在半年之后,“钱先生就写了一篇关于王元化先生的文章”。
实际上,作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钱谷融成就斐然:他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曾经引起广泛的论争,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如今都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等,都是文学学科的基础文献和必读书目……
今年恰逢钱先生九五华诞,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包括文论卷、散文译文卷、对话卷、书信卷在内的四卷本 《钱谷融文集》。文集收录了他有关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涵盖了其“文学是人学”观点的阐述,及对鲁迅小说、曹禺《雷雨》的研究;辑取了有关文学、人生的感悟随笔,与友人、学生的谈话,并收存了四百多封信札,富于思想艺术性和史料价值。
老一辈学人中,钱谷融的四卷本文集可能是最少的。他的好友徐中玉先生的文集有六卷,同为中文系的老教授王智量的文集有十四卷。在作家赵丽宏看来,钱老是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文集规模最小,但含金量都很高。”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自嘲道,即使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些同道中人的产量,都已经超过了钱老,这是很惭愧的事情,“眼下很多人太有所为,也因此很多地方就不能够做到从心所欲。钱谷融先生虽然所写不多,但真正做到了自由自在”。
当然钱谷融的“文集”之所以能“以少胜多”,重点在于其原创性。评论家毛时安表示,高尔基并没有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话,钱先生只是相信了这样的误传,所以做了“引用”,“实际上,这句话就是钱先生说的,是他的专利”。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伯海也表示,“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有一定的原创性。“‘以人为本’的观念,我们古人讲过,亦即‘人文’;西方近现代也讲,但他们讲的是个性意义上的人。而钱先生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到自己的文学活动中去。他的‘文学是人学’理念中的‘人’,既是活生生的个人,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同时,他也不只是说文学作品要写人,主要是文学要从人出发,以人为表现对象,以人为价值评价标志。这些思想都有相当的原创性。有些人以为这个理念过时了。我说不过时。因为谈文学主体性也好,谈消费主义也好,说到底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文学是人学’的理念。”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特别钦佩钱先生的文字表达,在他看来,钱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温和平实,没有剑拔弩张的火药气,在娓娓道来中谈清楚了很多问题,仔细体会,还能感觉到他的文字里有一种诗意。“看现在的报纸、网络,语言表达更新之快让人咋舌。有些人甚至不惜以背叛的方式来‘丰富’中文,但所有的背叛、挑战、创新,都有一个前提:作为‘反叛’的对象的中文,它本身有着很稳定、深厚的风貌。如果没有这风貌在的话,所谓‘反叛’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因为很多所谓‘极致’的表达,失落了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中文的内在的魂。而钱先生的文字,有这样的魂。他的文字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这正是我们今天读他的文章要特别加以珍视的。”
谈到钱谷融注重文字表述,圈内人都知道,考他的研究生都要考作文,而且他把写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