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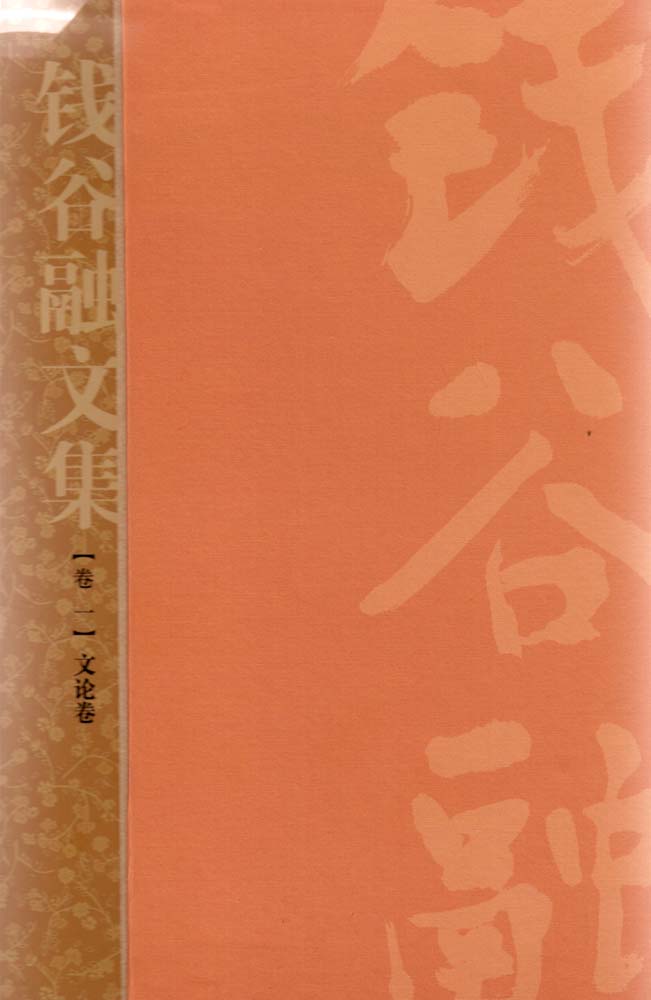 因为编辑《钱谷融文集》的缘故,我们有幸多次上门拜访“九五至尊”的钱先生。 因为编辑《钱谷融文集》的缘故,我们有幸多次上门拜访“九五至尊”的钱先生。
记得第一次登门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走进华师大二村,却别有一番静谧与清凉。一步一步,踏上褪色掉漆的木楼梯,吱呀声响仿佛诉说着岁月风雨,斗转星移。来到三楼,早已约好的钱先生弟子、华师大中文系杨扬教授为我们开了门,钱先生也从里面缓步迎了过来。天热的关系,先生穿着白色汗衫和睡裤,随意而愉快。不过,此后我们多次拜访,老人却都穿着西装西裤,头戴小帽,我们问他是否等会要出门,他说非也,平时在家就是这么穿着的。这倒让我们对钱先生的“散淡”有了些别样的认识。老人高寿,却依旧思维敏捷,动作也并不怎么拖沓,走路不用搀扶或拄杖,甚至能自己弯腰捡取物品。若不是我们拦着,还要亲自为我们倒茶倒水,谁能想到,这是位年届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先生呢。
钱先生招呼我们在客厅宽大的沙发上坐下,愉快地闲聊起来。一通新闻旧事聊罢,就说到了文集,我们说,这次编集,既是为您九五华诞留存一份纪念,又是为上海的文化老人整理出版学术成果,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荣幸,更是我们的应尽之责。钱先生微笑着表示感谢。于是,我们首先请钱先生确认了编选的篇目和分册目录,并将所有的著作文章按主题和文体分为文论、散文译文、对话与书信四个部分。钱先生特别关心自己早年的作品,询问是否收录进去。我们知道他对少作有特别的感情,便一一指给他看,《怀古说》《嘉陵江畔》《论节奏》《形式与内容》……都已经纳入目录,他这才满意地放下心来。正如后来陈子善教授在座谈会上讲的,要了解钱先生“文学是人学”这些观点是哪里来的,先生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早期的文章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
定下了篇目,茶几上早已准备好了三大箱的照片,供我们拣选,以作为文集书前的插页图片。打开纸箱,仿佛翻开一段私人的历史,钱老与夫人早年的结婚照,五十年代的标准照,七十年代的工作照,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照,九十年代的交游照,晚年的家庭生活照等等,黑白的、彩色的、泛黄的、褶皱的,全都翻涌出来。我们不时会让钱老辨认其中的人物,仿佛观看当代儒林的影像长卷,他则一一对答上来,大多还能说出拍摄的地点和年代,记忆力着实惊人。最后,我们共同选定了十来张钱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他欣然认可。
此后,为了将文集做得精致美观,我们又特地去请钱先生题写文集名和分卷书名。钱老的字不拘笔法,也是散漫随性而写,但搦管挥毫一点也不发颤、发抖,下笔并不拖泥带水,“文学是人学”、“灵魂的怅望”、“有情的思维”、“闲斋书简录”一气呵成。为了增加文集装帧的趣味和文气,我们又请钱老钤章,他从抽屉里捧出一堆印章供我们挑选,并说,你们自己盖就好了。于是我们也不客气,将名字章、闲章悉数印下,这里除了多种“钱谷融印”外,还有“不逾矩”、“文学是人学”等等,都是度身定制,颇能代表钱先生的风格和性情。
题字的时候,正好参观了钱先生的“闲斋”,与想象中不同,这里并没有什么宏富的藏书,据说是已经散书分送了朋友学生,现在只留下一些西文书和钱先生自己的著作。
每次我们都来去匆忙,怕影响老人休息,也未敢轻易邀约他到附近吃饭。后来才在该书出版座谈会上听到了他学生透露的长寿四大神菜“清炒虾仁”、“清炒鳝丝”、“砂锅鱼头”、“碳烤猪颈肉”,也听说了钱老对饮馔的执著,这不如说像他生活气脉的一个小小缩影。其实自称“懒惰无能”的钱先生,终究都有着艺术的执著、趣味的执著、生命的执著吧。就像他给外孙的信中写的,“一个人总应该有志气,应该活得硬朗、挺拔,遇到任何困难,都能不屈不挠”。下次有机会,我们一定要请钱先生吃饭,点上那几个他钟爱的神菜,听他讲讲生命中那些有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