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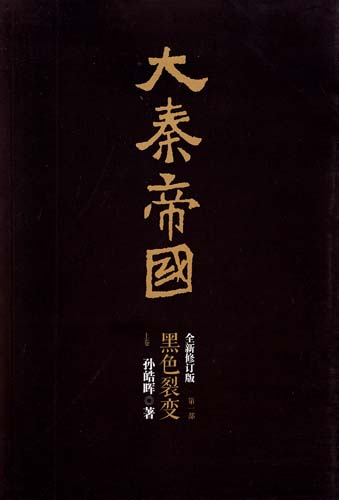 董健先生的《“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一文,以“谈话”的方式,对孙皓晖先生的历史文学巨著《大秦帝国》进行了从文学到历史、从历史观到思想文化、从动机到结果的尖锐批判。作为和董健先生一样的从极左年代和“文革”历史走过来的一代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以义愤代替说理,以臆想、推断代替分析研究的方法,以现实的需要代替历史事实的观点,不仅对于孙皓晖及其《大秦帝国》不公平,对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有害无益,对于当前文学和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入反思和讨论也是不利的。 董健先生的《“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一文,以“谈话”的方式,对孙皓晖先生的历史文学巨著《大秦帝国》进行了从文学到历史、从历史观到思想文化、从动机到结果的尖锐批判。作为和董健先生一样的从极左年代和“文革”历史走过来的一代人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以义愤代替说理,以臆想、推断代替分析研究的方法,以现实的需要代替历史事实的观点,不仅对于孙皓晖及其《大秦帝国》不公平,对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有害无益,对于当前文学和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入反思和讨论也是不利的。
一、《大秦帝国》及关于秦文明的“正源说”是一个可以并且需要讨论的历史文化命题
早在2009年4月,在为有关方面拟在北京召开的《大秦帝国》研讨会准备的论文中,笔者就在《一部规模空前的中华文明史诗》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笔者并未能与会,只是将文章交给主办方,会后《文艺报》以纪要的形式,署名发表了该文的部分内容。后来全文虽然收入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关于《大秦帝国》讨论资料一书,但影响范围很小,因此这里有必要摘录、重申当时的观点:
中国是一个具有三干多年文字史的古老国家,史籍的完备固然抑制着中华民族对于古史的神话想象力,却也发达着它在历史文学中的史传传统。由于官方史传的潜移默化,就连民间的文学艺术也常常打上了“统治思想”的深深印痕。进入近现代,列强所恃持的先进科技及新的“世界意识”,对中华帝国的屡屡侵犯,极大地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检讨、反思中国历史文化的潮流中,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类似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就是“吃人”的中华文化“原罪”说。持这种彻底的历史否定论的人们,固然有其渴望中华富强的良好动机,但却也使历史虚无主义“必然而合理”地成为相当长时期的中国社会主潮。其在历史、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文革”前后的几十年间一部中国历史,变成一部“农民起义”史,除了农民起义以外的历史文学,几乎都在禁绝之列。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华的富强和对世界重新认识,一种科学公正的中国历史意识和“世界意识”才日渐回到中国社会及知识界的视野中。然而囿于以往的种种禁忌和偏见,在历史文学写作领域虽有局部和个别的突破,但是在整体上却没有颠覆百年来的“原罪”史学的重要作品出现。当此之时,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不仅以其500余万字的长度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的建立与灭亡过程的巨大规模,而且以其鲜明尖锐、颠覆性的思想观点,在文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如,他关于不是被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肯定的周代的“仁”“礼”传统而是秦帝国的“变法图强”传统是中华的“文明正源”的观念,他关于秦帝国非“暴政而亡”而是关外六国复辟势力和秦始皇、李斯“失误”的历史“偶然性”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他关于由秦赢政开始的所谓“东方专制”的历史合理性的观点,他“非儒敬法”(与“四人帮”当年搞影射“周公”的“评法批儒”事件无关)彻底颠覆中国以“儒”“道”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史的观点,他关于“焚书”、“坑儒”的“真相”还原和肯定其历史正当性的观点,……等等,都将在中国史学界、思想史界引起巨大的争论。
所有这些都需专门的史学家和思想文化史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讨论。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天这场立足“高端文明”(孙皓晖语)的讨论,既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更有重新定位中华文明传统、弘扬民族传统精神、“重铸”(雷达语)民族性格魂魄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孙皓晖由一个经济法史学者,转而以文学艺术这种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写《大秦帝国》这部历史小说的根本动机。难得的是他的转行,既是对于秦帝国在中国历史的重大关头,立法创制,实现了由“封侯建制”到“郡县制”,建设统一的华夏文明,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热情,又是出于对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再造一个新的中华文明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迥异于当代许多舞文弄墨者的另一种文学的高度,别一种人格精神的风景。它让人想起在个人精神及肉体遭受了当权者残酷羞辱后,为了“明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发奋著史的史圣司马迁。如果没有这样远大的志向,放弃已经实现的教授、专家已有或可能有的种种诱惑,辞去公职,“放逐”自己于人生地不熟的天涯海角,甘于寂寞数十个春秋,完成如此煌煌文学巨著,是不可能的。如此定力,在当代作家中可以说十分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