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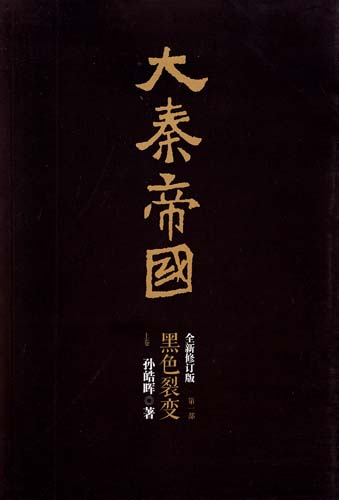 写下不一样的大秦帝国 写下不一样的大秦帝国
学者孙皓晖想呼唤的是——
1997年,西北大学给教授孙皓晖两年的创作假到期了,可《大秦帝国》还没有写完。他索性辞职,带着夫人去海南,闷在小屋里写了十多年,因为“在海南没有人理我。”
直到2008年,他完成了这部五百万言,六部十一卷的著作。回头一算,居然写了16年。
近十年来,这部书都是最常销的长篇历史小说。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的文化类推荐书目中,《大秦帝国》是其中之一。
小说中,孙皓晖把战国后期齐、楚、燕、秦、韩、赵、魏七国群雄并起的历史,铺展开来,描绘了近200年的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而小说之外,对秦文明的误解,依旧存在,孙皓晖认为,这不仅阻碍了对历史的客观观察,更影响了我们如今对改革的正常思考。
“我们总说现在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我们把春秋战国的变法浪潮进行深入研究,这石头就能摸得更好一些。”
用16年,构建大秦帝国
在海南,孙皓晖和夫人住在海口市一个类似于企业家属院的小区。很多人不解,既然写大秦,为何不近水楼台在西安原地?
在他眼中,西安的文化圈子太大,就算是不主动卷入,也有时时被卷走的可能。“你将被无数的零碎,分割得有心无力。在这一点上,海南要好许多。”
在一间小屋里埋头写作13年,用穷经皓首这样的词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孙皓晖过去不喜欢秦腔,但在海南,他却开始对秦腔有了感情,并且学会很多唱段。他还对秦腔《苏武牧羊》做了全面的改编。原本的戏词是这样的:汉苏武在北海身体困倦,忍不住伤心泪痛哭伤怀。孙皓晖不解:“一个老忠臣没事做了哀叹自己身体困倦?这可不可能?这是忠臣情怀吗?”他自己做了修改:汉苏武在北海将南天望断。秋风起边草黄年复一年。恨胡人剥去了我汉家衣冠。白发生鬓节折我心志更坚。
年复一年,是苏武的心境,也是孙皓晖的。只是苏武用了18年,他是16年。写《大秦帝国》期间,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于我,书海、人物、事件,日夜不休地纷至沓来,常常觉得脑子不够用,没有时间去孤独,去寂寞。从开始没人理睬我到后来慢慢有人理睬,这些我们都要能适应。”
有人说他是隐士。他有点意见。
他认为,隐士是一个后来的概念。前三千年,名士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没有人隐。后世把明哲保身、激流勇退者称为隐士。“有人说过我是隐士生活,去做一些从根本上厘清文明领域的事,甘愿清淡和寂寞。本质上我们不是隐居,我们始终心怀天下。我们虽然距离旋涡比较远,但是我们始终关心着民族的进程。”
孙皓晖选择写下来。“如果在风雷激荡的国家危亡时代,每个人的个性可能会更鲜明。和平年代只能通过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想法坦诚地告诉人们、告诉社会。这也是一种共建。”
汉到清,被看作“无所谓时代”
这条民族进程之路,在孙皓晖看来,是从秦帝国开始的。
这些日子,他依然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做讲座,“秦文明”“中国原生文明”“中华民族强势生存”,都是这样尖锐的主题,所行之处,他的主张总是语惊四座——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都是文明衰退、文明复制的时期,而中国历史最好的时代、古典文明的最高峰,是在春秋、战国、秦帝国,而它们恰恰被后代歪曲误解了。
经年沉积的误解,是他发狠心要写完这部书的动力之一。
“我们对秦帝国的扭曲,甚至妖魔化,从秦末贵族复辟势力开始,经西汉定型,一直持续了两千余年。最重要的是,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执修史大权,在史书中全面否定秦帝国与春秋战国三大时代,形成了我们对中国文明史的严重误读。”
在我们的思维定式里,秦是“暴政”,汉唐是“盛世”,但在孙皓晖的字典里,这些条框通通不存在。他把汉到清这2000年看作是历史上的无所谓时代。所谓太平盛世,对于当时结束分裂和战乱来说是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文明的意义上并没有多少创造性发展。“我们现在应该越过无所谓的时期,直接和我们的阳光时代对接,这就是为什么要去发掘秦文明的意义。”
之前,孙皓晖还在做一件很较真的事,就是把所有两千多年来,咒骂秦帝国的内容全部找出来,一一进行分析、评点,汇成一个“中国历代非秦评秦言论汇编评点”的集子。
当然,这些年,他也感到了一丝变化。主流历史学界对秦帝国的功绩,已经有了基本立足于正面的评价。“但是,作为民族精神的社会化认同,我们对秦帝国的统一文明正源的地位,仍然远远没有达到社会共识的程度。就是你自己,也可能随时顺口说出这熟悉的两个字——暴秦。没有基本的社会共识,就还不是普遍的民族价值观。”
学习正面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们没有忘记秦帝国,但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创造力却淡漠了。这是孙皓晖在《大秦帝国》序言里的感叹。事实上,秦帝国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在规范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