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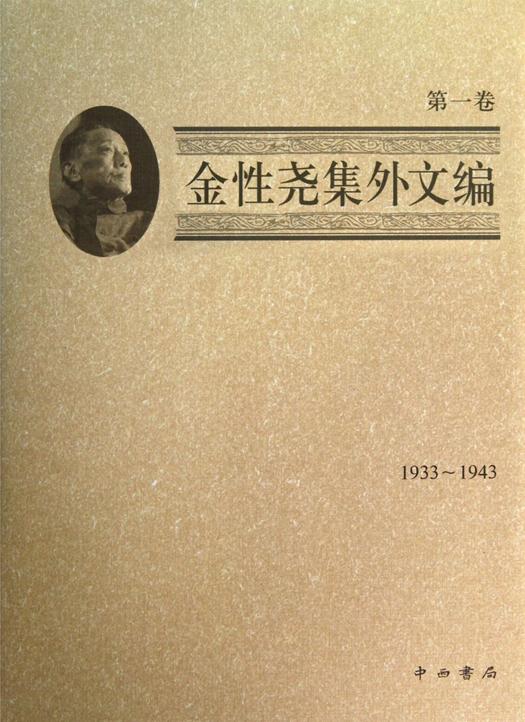 2009年,九卷本《金性尧全集》出版,收录了金先生生前列已梓行的各著作,弥足珍贵。最近,《全集》的集外文部分由金先生三女金文男女士辑录而成《金性尧集外文编》四卷,使先生自1933年以来未曾结集出版的各类文章以及古诗文赏析、作家小转、编辑手稿、旧体诗等皆能到得读者眼前,其搜觅之艰辛与编辑之烦难,有心的读者都会感激。 2009年,九卷本《金性尧全集》出版,收录了金先生生前列已梓行的各著作,弥足珍贵。最近,《全集》的集外文部分由金先生三女金文男女士辑录而成《金性尧集外文编》四卷,使先生自1933年以来未曾结集出版的各类文章以及古诗文赏析、作家小转、编辑手稿、旧体诗等皆能到得读者眼前,其搜觅之艰辛与编辑之烦难,有心的读者都会感激。
四卷集外文翻读一过,真是叹服金先生的笔耕之勤。前三卷所录文章总数达558篇,而内容既有针砭时弊的杂文、闲谈文史的随笔,亦不乏读书有得的札记,评骘甲乙的书评。尤其晚岁,先生或感年光促迫,写作更勤,耄耋之年,仍坚持日写二千言。而单以文章论,早年文字显然深受二周影响,凌厉峻刻,感时伤世,尤其不满国民性中的庸劣与智识阶级的市侩气,手起笔落,竟忽忽有沉痛之音。至于出入文史,检点群籍,却始终以一己之意裁断古今,不比炫才的酸腐秀才,但知夸多斗靡牵扯成篇,想必熟悉金老文章的读者都自有感会。
此番集外文的汇编出版,在让读者读到更多金先生散落在外的佳文秀什之外,我以为更要紧处,在于第四卷的古诗文赏析、作家小转、编辑手稿、旧体诗,这些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了作为编辑家与赏鉴家的金先生。
长久以来,金先生从事古籍及文史书籍的编辑审读工作,本书收录了28篇编辑手稿,皆录自出版社档案。其中两份比较重要的文本是关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及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的编辑意见。就前者而言,我们当可看出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在27条修改情况说明中,几乎全系为了适应当时的现实情况而作的修改,诸如认定“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继续和发展”、“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春秋战国散文的发展“是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思想特征的反映”,对庄子的评价则从全盘肯定修改为批判庄子“对于政治斗争和自然斗争完全失去信心”、“把人引到弃绝人世的太虚幻境中去”,彰表扬雄“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并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已经接触到农村问题的核心”。由今观之,当觉上述表述实在荒诞不已,但恰是这份修改情况说明,为一个荒谬的时代留真存影,以此体认当年的学者是如何在书写历史与符应现实中做出一己艰难的妥协与坚持。
之于《金明馆丛稿初编》的编辑意见,则颇见出金先生的识力。他指出陈著之长处在于一“能从某些历史现象中揭示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并善于将资料排比归纳,探索渊源”,因此令读者读后有“左右逢源”之感,在作者则成一家之言;二是陈著“能够注意他人所不注意的历史生活的细节,颇多发人所未发处”。至于短处,金先生亦不客气,直言陈寅恪有时“颇多牵强附会”,有“英雄欺人”之处,并认为此老之一病恰如鲁迅所说“专门家之言多悖”,认为陈所谓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缘溪行”之“溪”乃谿族之“谿”,实为妄诞。不过更令我佩服处,尚不在金先生的识见,而是其虽觉陈书时有不尽情理处,却坚持认为“作为学术上的见解”,并“不准备提请作者修改”。识见来自金先生的学养,不请修改则源于金先生的职业操守,老辈风范于焉可见。
而占编辑意见大宗的则是金先生对于多本文史普及读物的具体审读意见。要之,他以为作为文史普及读物,要以“简、浅、精、准”为原则。所谓简,是指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绍介简明扼要,不拉杂比附,故其批评《陶渊明诗文选》的作者串讲繁芜,“几乎等于陶集的编译”;所谓浅,是指释解典故、赏析文字时,照顾到大多数读者的程度,不必矜才使气,故其一再要求作者注释译文要能“平稳通顺”;所谓精,是为便于读者省览,应要言不烦,审读意见中他对《古代游记选》批评甚多,认为是书体例不一,注文连篇累牍,看似详博,“实则对读者毫无用处,只嫌烦琐”,而用语文风“普遍存在于普及读物精神不相适应的古色古香现象”;至于准,则是切实朴质,金先生时常在意见中点出作者“浮文稍多”,如批评《历代书信选注》的作者前言“泛泛而谈,语多重复,文字也稚嫩”,批评《清代散文选》的作者前言亦是“太笼统空泛”,而所谓的笼统空泛,其实皆肇因于作者自身的修养,故大多只能做到古人所谓“仅标来历,未识手笔”,更陋者识断柴塞谓肿曰胖。
显然,金先生自己对于文史古籍的赏析注释,也抱持着上述的悬格。昔年《三百首新注》系列一时风靡,不啻是文史爱好者的梯筏津梁。而卷四收录的自1984年至1996年见刊于多种古代诗文赏析读物的文章120篇,则更让我们见到作为赏鉴家的金先生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