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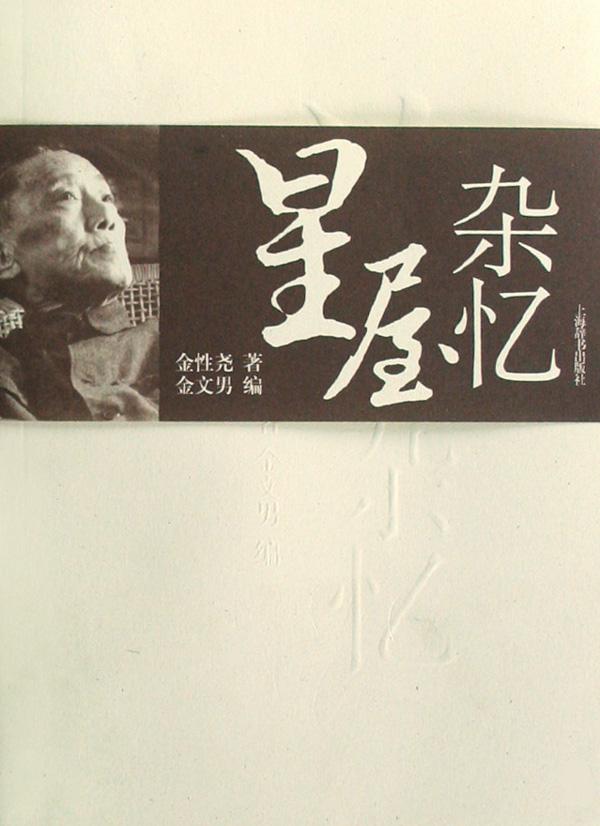 听说金性尧先生的全集已经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正巧在书店里翻到一册《星屋杂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顾名思义是怀人忆旧之作。金性尧生于1916年,2007年去世,这本书差不多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相关文章,一路读过他著作的读者几乎不必再尝鼎一脔了。但此书有一篇长达36页的代前言,出自金性尧的女儿、也是该书编者的金文男女士之手,正是这篇类似小传的文章《我的父亲》,才使得旧文章有新意思。 听说金性尧先生的全集已经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正巧在书店里翻到一册《星屋杂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顾名思义是怀人忆旧之作。金性尧生于1916年,2007年去世,这本书差不多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相关文章,一路读过他著作的读者几乎不必再尝鼎一脔了。但此书有一篇长达36页的代前言,出自金性尧的女儿、也是该书编者的金文男女士之手,正是这篇类似小传的文章《我的父亲》,才使得旧文章有新意思。
星屋是金性尧的别号,他还有一个较知名的笔名文载道。曾经在香港的旧书店里翻出好多翻印的民国丛书,包括周黎庵的《吴钩集》、《华发集》等,文载道的《风土小记》也在其中。后来才知道周、文两位就是十多年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经常“见到”的周劭和金性尧。后来陆续买了金性尧的《伸脚录》、《一盏录》等书,但是单看这些书并不能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这正是《星屋杂忆》值得称道的地方。金文男女士的长文分为:家世、私塾生活、婚姻、和鲁迅的四通书信、编辑《鲁迅风》、主编《萧萧》、为《古今》撰稿、主编《文史》、忘年交周作人、古典文学编辑、因议论“蓝苹”得祸、大姐冤死之后、视写作为生命及晚年的痛苦,共14个章节,其中着墨最多的是他的职业生涯,而金性尧因孤岛期间为《古今》杂志撰稿,“成为困扰他一生的沦陷时期的历史问题”。这种说法对其子女来说,是充分说明问题的:金性尧的历史问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某些灾难正是体现在他的家人身上。对于这段历史,金性尧也坦诚告解,自省自责见于言表。他在《悼黎庵》一文中说:
“后来和黎庵合办了《古今》,朱朴是没有金钱和权势的,但因投靠了周佛海,经济上也有了保证,成为周门一个高级清客。我也是相差无几,后来是自甘附逆。作为《世纪风》的作者原是很清白的,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政治上便有泾渭之分。抗战胜利后被人诟骂,也是咎由自取。每个人的行动都应由自己负责,我是自己撞上去的。因为这时候我正在吸鸦片,需要钱用。这真是百悔莫赎的恶果,我一生的许多错误,皆由此而来。为了此事,我们夫妇之间也筑了一道墙。”(P120,此文最早刊于《万象》杂志2004年第一期,关于金与《古今》的关系还见《借古话今》一文)
《我的父亲》还披露了很多家庭细节,这些细节差不多构成了金性尧一生中的重大关节。比如定海金家的发迹,比如金的夫人武桂芳女士在三十年代以“木圭”为笔名创作小说,是孤岛时期颇为活跃的女作家之一;因为与许广平来往密切,曾被日本人抓走;想去延安参加革命,金性尧亦未反对,还是因为金母发现了才未去成。姜德明先生的书话里曾经提到武桂芳发表在《燎原》杂志的小说《菩萨奶奶》,补白大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也提到过这对醉心新文学的夫妇,但可以想见,各种历史际遇之下淹没了这些细节,连人物本身的面目也模糊了———这是从《风土小记》读到《饮河录》都很难拼凑出的影子。
正是因为这篇长文,再来看此书选录的怀人忆旧文章,则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从个人的遭遇来体会文学作品的倾诉与寄托。早期的文章,正应了金文男女士说的“1934年,父亲18岁,是个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如收录在《风土小记》当中的,可以看出金性尧最早走的是文学道路,文章更近于我们常说的散文,多议论,白描、叙事较多,颇有抒情的味道,也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风气,但也有他个人的追求。金性尧晚年在《散文的境界》中说,“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点缘,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酽然之味,而不流于空疏”。这可能是他早期的文章不随时代湮灭的原因。到后来弃文入史,文章虽掌故居多,下笔却有种极有分寸的感情,最感人的莫过于他对家人对朋友的厚道。怀念妻子的《一个声音消失了》里面说,“夫妻之间的争吵摩擦更是难免,一旦存殁相隔,连从前的星米之争,也成为永难重现的怅惘”,极其真实的心态,对母亲及夭折的女儿虽愧疚不同,但“人生最受难的时节,就在清夜扪心这一过程里”。他对女作家苏青的宽容,对回忆周作人的审慎,“文革”中“配合”外调人员“了解”自己朋友何家槐的内疚,都非常的有人情味,像盐一样,调和了金性尧怀旧短文章的深沉味道。或许,在我们读过他的人生阅历之后,能获得一个视角,更宽泛地了解他的世界。
最近还看到一本很“拼凑”的书,梁实秋的《雅舍遗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5月版)。晚年梁实秋给台湾《中华副刊》的蔡文甫回信:“老牛奶已挤干,勉强挤,挤出来的奶,质量均差,而且痛。理宜放诸牧场休息也。”这虽是俏皮话,但这种痛感,恐怕是晚年的“文字工作者”如金性尧梁实秋们的人生密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