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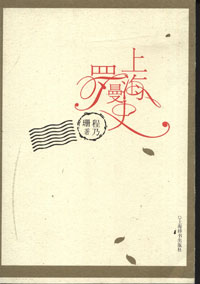 “有怎么样的城市就有怎样的女人。”海派女作家程乃珊曾在书里这样写道。而她自己,正是这座精致城市里优雅女性的代表。她写上海的故事,她也是上海的故事。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定义她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人们从她的笔下“还原这个城市贵族的尊严,高雅而温馨”。 “有怎么样的城市就有怎样的女人。”海派女作家程乃珊曾在书里这样写道。而她自己,正是这座精致城市里优雅女性的代表。她写上海的故事,她也是上海的故事。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定义她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上海小资情调的开拓者,人们从她的笔下“还原这个城市贵族的尊严,高雅而温馨”。
今年4月22日,程乃珊因为白血病不幸病逝,享年67岁,令上海文坛震惊。今天上午,程乃珊人生告别会及安葬仪式在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举行。其丈夫严尔纯先生及百余位亲朋好友,一起送别这位上海的女儿。
程乃珊丈夫严尔纯先生昨日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从乃珊得病到去世的16个月里,他寸步不离、悉心守候在爱人身边,并一直鼓励她“相信科学,你的病会好的”。回忆最后的时光,严先生几次哽咽,因为“分分秒秒,都历历在目”。 “她闭着眼睛口述,我笔录,录完一看,几乎不用怎么改动。我表扬她,‘看不出你还有这个本事啊! ’”就在乃珊去世前的一个月,她完成了生命中的绝笔——散文《用生命烹煮的咖啡》。
程乃珊的“新居”坐落在福寿园内。这里已有六百余位上海名人将自己的人生典藏于此,在这方土地上化为一股韵味悠长的独特的上海之味,给城市留香,给未来品呷。想必这位爽朗健谈的 “沙龙女主角”、“上海Lady”不会感到寂寞。
思念
67年的生命,44年相濡以沫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眼看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的人自己才能真正看见的……哪怕是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断的风韵,这像家里那几支早已老去的勿忘我。
自从你病后16个月中只有我一直守在你身边,你的挚友和学生轮流来陪伴和陪夜。家里的一切都围绕着你转,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当然还是违背你意愿而忌吃的东西不能满足的,怕细菌感染把我们养了12年的老狗送了人,这也是你我心头之痛。每次我在遛狗时总对它说“Bobby,实在对不起,你和妈妈之间我只能舍弃你了,实在对不起! ”那天送它走时,它却躲进了妈妈的床底下,非常心酸。
人生只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乃珊,你一步一回头地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什么也抓不住,我的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
但是,如果没有你们这么多朋友的关心和慷慨帮助,我可能就是让人怜悯的角色,你们用你们各自的方式关心我、宽慰我,让我开心,我衷心感谢你们,所以,我必须开心。让乃珊放心!让乃珊安心!
■忆夫妻间点滴
“永远有讲不完的话”
“44年的婚姻,虽然是老夫老妻,但情感从来不曾淡漠”,描述起和妻子程乃珊的婚姻生活,严先生这样向记者描述,“一直很热闹,对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话题,我们永远有讲不完的话”。
严先生说,程乃珊特别喜欢看当时的外国译制片,而且对电影里的情节、台词、细节有惊人的记忆力。 “我也喜欢看电影,她跟我聊起时,我总能聊得上”。 “有一次,两人都准备去卧室休息睡觉了,程乃珊随口讲了一句电影里的台词,‘格列布,我们都疲倦了’,我看过这部电影,记得里面有个配角的台词,我立马接上去说‘要不要给你一双拖鞋’,当时程乃珊大为惊讶,一下子就乐了,‘你这个戆大也晓得这部电影? ’……两人的默契建立在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上。严先生交谊舞跳得好,他手把手教程乃珊跳舞,后来成为朋友圈里公认的舞技一流的夫妻。
“她的笔下有我的所见所闻”
1984年,程乃珊的中篇小说《蓝屋》获首届“钟山”文学奖。《蓝屋》的生活原型是“绿房子”,这个位于铜仁路上嵌着绿色砖面呈弧形的四层建筑,出自犹太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之手,它的主人是老上海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吴同文。
程乃珊曾回忆道,小时候她经常路过绿房子,知道里面有很多故事。特殊时期,遭到批斗的吴同文选择了自杀,他的姨太太也陪着一起自杀了,两人手拉手死去,到发现时,别人怎么拉也拉不开。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一直觉得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没想到上世纪70年代,她结婚了,自己的先生就来自这个房子,严尔纯是吴同文的外孙。
程乃珊生前曾经多次感谢她的丈夫,因为许多对于“蓝屋”的了解,都来自于丈夫的讲述。 “她写很多老上海故事的时候,写不下去了,或者对细节感到模糊,会来问问我,比如过年的时候年夜饭的情景,听了我的描述,她就能从中提取一些灵感,我很高兴,她的笔下有我许多的所见所闻”。
可以说,程乃珊夫妇都出自老上海的名门世家。程乃珊的祖父程慕灏先生,是当时著名的银行家,而严先生的外祖父则是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吴同文,两个家族都有坎坷曲折的传奇历史。严先生说,也许正是两人都有类似的家庭背景,都出自大家庭,让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并能彼此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