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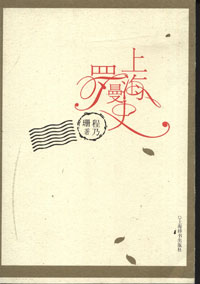 “日日见到的那个街口摆修阳伞摊的老头子一夜之间抖掉几十年的霉相,被锃亮的小汽车接走了,原来他是昔年上海滩的金融巨头,今华尔街某银行老板还是他昔日的学生,随后人们频频在媒体荧屏上见到他;当年抄家时将资本家往死里整的那个小将从深圳淘金回来已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一个以做保姆为生的孤老在为东家擦窗时不慎跌下身亡,贴身缠着的腰带内各种金刚钻、翡翠、白金块滚了一地,原来她是隐姓埋名多年的某位上海名媛……”这是程乃珊记忆中1980年代上海的故事。 “日日见到的那个街口摆修阳伞摊的老头子一夜之间抖掉几十年的霉相,被锃亮的小汽车接走了,原来他是昔年上海滩的金融巨头,今华尔街某银行老板还是他昔日的学生,随后人们频频在媒体荧屏上见到他;当年抄家时将资本家往死里整的那个小将从深圳淘金回来已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一个以做保姆为生的孤老在为东家擦窗时不慎跌下身亡,贴身缠着的腰带内各种金刚钻、翡翠、白金块滚了一地,原来她是隐姓埋名多年的某位上海名媛……”这是程乃珊记忆中1980年代上海的故事。
1980年代的上海与1940年代一样充满传奇,后者归了张爱玲,前者便归了程乃珊。
她始终记得,当花样年华的他们遭遇了变革后的大时代,一潭死水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传奇”二字令他们羡慕欣喜、烦躁和蠢蠢欲动。即便在二十年后回忆起那个时代,她依然保有热情,她写道:“传奇是大时代在蜕变转型中不同价值观和审美观互相碰撞后促成的机会和提供的空间,为了追逐传奇,原先稳定的婚姻破裂了,随遇而安吃大锅饭的平静心态给打破了,深埋多年的难解情结袒露了……街头巷尾,饭后茶余,听到不少故事,我就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因此有了《蓝屋》,有了《穷街》,有了《女儿经》……”她把一切都归于时代,而自己退居记录者的身份,殊不知久而久之,她也变成了传奇。
从蓝屋到绿屋
1983年,程乃珊凭借《蓝屋》获得《钟山》首届文学奖,轰动一时。小说的内容很简单:主人公顾传辉寻亲偶然发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当年1930年代上海滩的豪门巨富,顾传辉出于私心对豪宅蓝屋充满向往,而顾传辉的父亲、中学教师顾鸿飞,当年为了追求自由理想的爱情而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从蓝屋出走,对顾传辉的想法嗤之以鼻。最后顾传飞终于明白在不劳而获的贪欲和自尊自强的奋斗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在小说中,“蓝屋”代表着过时的奢靡精致的生活方式和不求进取的生活态度,这与我们印象中程乃珊对“蓝屋”的原型——“绿屋”的喜爱无疑是违背的。而当我们将它还原至历史中,这一切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旧上海传统的流光溢彩的形象在主流话语中消失了,作为大都会的上海被置换为新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旧上海的情趣与市民日常生活被有意忽略或掩盖在“大历史”叙事的时代洪流中。“文革”时期,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令上海的城市文学销声匿迹,作家们都以描写工农兵和农村生活为己任,对于都市生活则往往不敢涉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程乃珊登上了文坛,写出了《蓝屋》。当年,围绕着顾传辉该不该回到蓝屋,甚至引起了一场社会大讨论。
陈村说:“当时她写的《蓝屋》,她的兄长去了西北参加建设,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所以这个兄长的形象在她心里也很重,她就愿意去讴歌这样的人物,我当时说她是毛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我觉得《蓝屋》这个故事中家里的本意是不成立的,因为人是不喜欢把自己的房子交给别人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写作总是会有一些扭曲,有一些言不由衷,对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她更为本色了,革命的话题离她比较远,她所欣赏的生活方式,她所喜欢的年代和人物,其实都不是那种要求进步的青年的形象,而是另外一种。所以后来她从这一面去写一些有关的老的故事、人物,才更像她。”
程乃珊心中终究是爱蓝屋的,她曾多次表示,她太喜欢“蓝屋”这个名字了,并打算重写《蓝屋》,“过去写得太肤浅”。此后,她一次次描绘起“绿屋”,这座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交界处的绿色砖面外墙建筑在她笔下矫枉过正,“犹如一抹烟笼翠绿的都市中的苏堤柳荫”。在《上海探戈》中,绿屋是“中西文化荟萃的风火炉中千锤百炼的一颗金丹, 闪耀着海派的华彩”。程乃珊对绿屋的迷恋和推崇,背后是她对海派文化愈加深刻的认同。
事实上,这栋昔日曾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墙圆形建筑背后所承载的沧桑历史和凄美传奇,一点都不输给小说。程乃珊与绿屋的传奇,也丝毫不输给小说的传奇。“绿屋”是由曾经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所建。房子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为其亲自设计。“文革”开始后没多久,吴同文就因经受不住打击而同姨太太一起在房子里牵手自杀了。这栋童年每每经过的绿屋给程乃珊留下了深刻印象,孰能料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结婚之时却忽然发现,原来她所嫁之人正是吴同文的后人严尔纯。
上海的非虚构写作
如果说程乃珊在1980年代所写的是当代上海,那她在1990年代以后所写的反而是那个“老上海”。
她曾对王小鹰说,现在涌出来很多写上海的作家,但是他们写的上海不真实,有很多扭曲的地方,尤其是写她那个阶层的生活,好像永远是醉生梦死的。而事实上,“她觉得其实像她的祖父这种金融家,是很辛苦很努力创业的,有了财富以后也不是挥霍无度的暴发户,而是有腔调、有品位、守规矩的,这才是老克勒。她写的老上海是贴肉的。”王小鹰说。
|